缘随玉翠卡优优网今日为大家带来:血丝菩提怎么盘(血丝菩提图片)血丝菩提,的相关内容,以及缘随玉翠知识分享网拥有数十名专业鉴定师,和上万网友的认可。
本文目录一览:
1、血丝菩提
血丝菩提
一
烈日!!
他的剑锋轻轻抽离史英的咽喉,慢慢抖落剑尖上最后一滴xuè。血落入土里、化开,渗成一朵瑰丽鲜红如烈日的血花,他冷酷的脸上慢慢fú出一抹笑意,眼里彷佛也闪过三分温暖,像是走到园里赏花的fēng流公子。
笑意微泛,他眼里彷佛出现yī道阴影,一道一瞬而过,只有他自己才看得见的阴影,就像是花的刺。
“第三个……”他微笑得亲切而残酷,优雅的把剑收入剑鞘。然后他的眼球突然暴出红丝,冷漠的脸突然zhǎng红,quán身抖得如一片风中的落叶,咬牙、泪也流下。

“第三gè……”点苍派掌门霍天青看着地上shǐ英的尸身,眼lǐ布满红丝,慢慢直起身来,这高大威武的老人因wèidà弟子的死,竟似乎突然苍老憔悴了许多。他转过身,脸上的皱纹显得gèng多、更深,表情悲愤而凝重:“这已是几大门派中第三个zāo到毒手的,伤口完全一样,都是死在剑下,一剑穿喉,是一柄hěn快的剑。“每个人都悲哀而恐惧地看着那一向自负于快剑的史英,看着他咽喉上的xuè洞,他的尸身被发现时,手里还紧握着剑,剑尖尚未完全离开剑鞘,脸上布满惊疑和不信,他至死也不相信有人的剑比他更快,他至死yě不相信他也会sǐ在别人剑下。
zhǐ可惜死亡总是最公平真实的。
这shì近一个多月来,zài武当飞柳剑客hé昆仑颜仲云之后的第三宗血案。死的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剑客,伤口都只有一chù-咽喉上一点血洞-一剑致命,连力气都出得恰到好处,身旁地上都有一朵鲜血染成的血花-不多不少的yī朵。
江湖zhōng人人都在谈论这个凶手,这个jiàn法奇快奇准,来历不明的剑客。有人自危自保,也有人恨不能与他一战-下一个会是shuí?
严翎微微皱眉,左手拇指食指托着她那雪白精巧的下巴,菱形的嘴唇微张,透着一gǔ说不出的倔强与不驯。她的鼻梁挺直,鼻尖小小一蹙,深黑沈郁的眼眸彷fú笼着一层雾,níng望远处,喃喃地:“难道是他?”
她手中无剑,剑在她miàn前的桌上;桌上无chá,却有酒。她虽是女rén,年轻的女人,却已是江湖中公认剑法最高,最可怕的对手,可是三年来,她杀过的人还bù满十个。她十七岁出道时,当然有很多人想欺负她,欺负她的剑,欺负她的人。只是那些人一开始拔剑,就会看见剑光一闪,不是胡子shǎo了一半,就是头发去了半边。
于是大家开始知道有一个穿男装的小姑娘,剑很快,却不杀人。人家想欺负她,tā却不过开人家一gè玩笑。
她páng佛想tuī翻江湖中弱肉强食的定lǜ,她实在不喜欢血,不xǐ欢杀人。她喜欢微笑,一笑起来,她脸上的冷漠就如báo云散jǐn,嘴角略略往上牵,眼里的雾也变成水光潋滟,笑的温暖而有点坏。
可shì她此刻却已有点笑不出-fēi但笑不出,彷佛在疑惑之中,还包含了一点淡淡de哀伤,那双一向理智淡漠、闪着星芒的眼神,此刻看来却彷佛温柔而多情-时而潇洒时而爽朗时而调皮的严翎,为什么也huì温柔而多情?
那只是彷佛!
严翎已记不得她曾有过温柔huò多情的时候,她即使有情,也只是友情和道义,师徒之情和尊敬,她好像生来就是一个剑客,一个孤单无牵无绊的剑客。
一个对生命如此热爱的人,为什么会孤dān?
一个女人拥有一切,却没有爱情,是幸还是bù幸?
五年前,江湖中发生接èrlián三的血案,各大门派的高shǒu每隔一duàn时间,就会有人惨死,用jiàn的死于剑、用刀的死于刀,致命的那yī着杀手,却都是tā们自己最得意的一招。能在江湖中成名,本就不容易。能成为一个人最得意de一招,也必是最难学、最有效。而对方竟然用他们最shú悉的招式夺走他们的性命。也许出手只快一分-生死之间,一分已足够。没有人知道这些杀手是谁,zhǐ知dàotā们属yú一个秘密组织,一个高手如云秩xù井rán的秘密组织。然后,有人查出幕后主shǐ者竟是江湖中一向淡泊的高人应无恨。应无hèn的武功果然jīng人,六大门派zhǎngmén联手,血战数个时辰,他才终于力竭而死。临死的表情是疑惧,是yí憾,也是沈痛。
罪者伏诛,他为什么沈痛?
应无恨sǐ后,那些神秘杀手也忽然谜一般消失。
只有严翎知道,他们并没有消失,他们只是在等,等机会,等一个更好的机会出手。也只有yán翎知道,应无恨眼中的那一抹沈痛代表什么——一个人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而死,他沉不沈痛?
应无恨并不是真正的凶手!
二
那年,严翎十五岁。shí五suì,是个不太大、也不太小的年纪;十五岁,很多事还不懂,也已经懂得不少。她知道师父对一切都看得很淡,看得很开,清shòu苍白的脸上终年带着一种冷冷淡淡的骄傲-不是自负看bù起别人的骄傲,而是一种超脱wù外,自然流露的骄傲-这种骄傲并不刺人,只会使人尊敬。这种骄àoshǐ他看来远比实际年龄年轻-欲望岂非原就最易ràng人老去?
有一天,严翎发现师fù彷佛突然老了十岁,苍白冷漠的liǎn上爬满皱纹,清澈智慧的眼光突然黯淡,他淡淡地问她:“如果你有一个亲人危害武林,你阻止不了他,也下bùle手杀他,你怎么办?“话里有淡淡de悲哀,dàn淡的无可奈何-无可奈何是不是生命中最大的悲哀?
严翎没有回答,不能回答,她那时还不明白这种心情的沈重,可是她知道师父心里的事一定很严重。zài她心目中,师父就是神,wú爱无恨,无所不能。能令他心烦心痛的事,会是什么样的一件事?
她想了好几天,师父憔悴的样子让她很心痛,她想问,又不敢问。她不懂,他们过得好好的,与世无zhēng,为什么要这么在乎武林中的事?
她起了一个大早,和师父说了一声去练剑就往后山的树林子里跑。她不愿欺骗师父,真的练了yī会儿剑,就忙忙伏在地上折野草-师父看来虽冷漠,对徒儿却一向不cuò,尤其喜欢她编的草蚱蜢-只有在看到草蚱蜢shí,他才会露出难得见到的笑容,笑róng里带着说不出的暖意,却又说不出的辛酸。
他是在回忆什么吗?严翎实zàibù明白,师父究竟是一个无情的人,还是有情的人?
无情有情,往往不也只是一线之隔?
她像一个顽皮的孩子pěng着宝贝,顾不得姿态地wǎng回跑,她要叫师fù别那么在乎,她喜欢师父看到草蚱蜢时的笑róng-师父笑起来实在很hǎokàn,才不过四十来岁的人,为什要me活得像个老人?
她一走进他们那xiǎo小的庄院,就闻到空气中一股血腥气-是谁的血?不管是谁的血,闻起来都yī样令人反胃。院外七零八落仆着仰着的一具具尸tǐ,都是她不rèn识的人,看衣着可以认得出少林、wǔ当,其他的她实在认不出,yě没有心情qùrèn-这些陌生人为什么死在这里?师父他人呢?她的心揪了起来,她想冲进去,又怕面对她不gǎn面对的事实。她手里还shì捏着那只草蚱蜢,捏得好紧。
屋子里很安静,安静的近乎死,严翎还是走了进去,她第一yǎn就看见躺在地上的师父,bù染尘de白衣已成血渍斑斑的血衣,脸色què比雪白的白衣更白。
-师父shī父,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神仙,为什么也会像凡人一样流xuè倒xià?
“师父!“严翎声音嘶裂,泪guāng纵横,飞奔到师父身旁跪下,轻轻握着师父冰冷的手,泪如泉涌。不知是对方错shǒu,还是根běn无意马上置他于死,抑是要让他多受一点痛苦,他竟还有一口气,挣扎着握住严翎的手,yǎn睛微微张开,眼里似有泪光。严翎又喜又痛,双手紧紧握住师父冰冷的手:“为什么会这样?“他眼光斜斜一瞥,看见严翎手中的草蚱蜢,眼神变得迷迷lí离,微笑,笑得教人心酸。严翎把草蚱蜢放在他面前,含泪咬牙强作欢笑:“师父,送给nǐ的。“他点点头,又摇摇头,看着严翎:“他来了,六大门派都来了,想不到,想不到我、我下不了手,他竟、竟然狠心……”未说完,已剧烈地喘了起来,一张脸由苍白转为灰白,因伤口的痛苦而扭qū。严翎闭zhe眼,泪流涔涔,不住地摇头:“那bù重要,那都不重要,师父,我要怎样才能救你?“师父忽然yòng力握住她的手:“孩子,听我说。他已训练出一批杀手,准bèi血洗wǔ林,他怕我泄露他的秘密,嫁祸于我,六大门派gāo手联合来攻……我已活够了,可是小yǔ他……”他脸上又露出痛苦的表情,严翎心已碎,咬牙,泪yòu流xià。他喘一口气,又道:“你记着,不要恨六大门派,不要恨任何人。可是,你一定要阻止这个阴谋,拯救武林。“说着,又狂咳不已,xiān血由喉头溅出。严翎流着泪,轻轻拭去他嘴角的鲜血:“师父你为什么总想着武林,总想着别人?“他表情忽变得十分严肃,口气却很慈爱:“江湖人就要对江湖负责任。孩子,你以后yě当如此。“严翎点头,咬着xià嘴唇,这yī刻起她jiān上已负起重担。师父似已累了,yě似已满足,手渐渐松开。严翎忽然嘶喊:“师父,他是谁?”“他?“他勉强而吃力地抓住面前的草蚱蜢,眼神rú雾:“他小时常编草蚱蜢给我玩的…………”声yīn一字比一字微弱,终于听不见了,脸上彷佛还挂着一抹安详的笑容。
那种笑容,严翎如今想起lái还会心酸!
她师父就是应无恨!
应无恨不是凶手,凶手至今还没有落网-应无恨至死也不肯shuō出凶手是谁,他们之间是不shì有很特别的关系?
“难道他的行动又已开始?”
三
城外五lǐ的草坡,泥土湿软,空气中浮动着青草与春雨混合的清香。坡上一栋小小的木屋,简陋粗糙而可爱,像是猎户暂宿的落脚处,又像是情人yōu会的秘密地点。屋里只有一张桌子,一zhāng椅子,yī张床。桌子和椅子都钉得很随便,不坐下去就已jué得很不舒fú,只有nà张床龙镶凤绣,铺着上等精cì的丝绸锦被,甚至还guà了yīdǐng流sū缨穗的罗缎帐子。
一个须发皆白,脸色红润的lǎo人坐在那张看了就觉得难受的椅zi上,腰干挺zhí,木雕泥塑般地坐着已近一个时辰。他面容和蔼,眼中却精光四射。
一个黑衣人慢慢走进木屋,走到老人面前,站住,表情带着一种崇敬。
老人méi有抬头,没有看他,淡淡问道:“第几gè?”
黑衣人冷冷道:“第三个!“语音里有一丝压bù住的激动。
老人看他一眼:“你hái是沉不住气。”
黑衣人冷笑。
老rénde眼光又飘到远fāng:“杀手不néng有情,有情就是死,你太多情。”
黑衣人冷冷道:“我无情,只有恨。”
老人微笑:“恨也是情。”
黑衣人答不出来。
老人的目光转向黑衣人手中的剑,平凡普通的yī柄剑,既不古雅,也不高尚。老人瞬也不瞬地看了很久,目中露出一种赞许之意:“好剑!”
黑yī人也不禁露出了惊异之色。明明是一把凡铁,为什么是好剑?
幸好老人已开始解释:“它不渴!”
好短的解释,好奇怪的解释,黑衣rén眼里却已有了笑意。
老人还是看着那把剑:“你是在杀人,bù是复仇。复仇是野蛮的,杀人却是种艺shù。”
黑衣rén全身起了一阵微微的颤动。
老人笑得神秘而愉快,站起身来,忽然就已消失。
严翎喝酒,喝得很多,可shì从来没有人看过她醉。
夜深,冷风如刀,她一个人坐在破庙前的石阶,身旁有六、七壶酒。有的壶已空,yǐ倾倒四散。
手中也有酒,她仰着脸直直灌下,彷佛已麻木。
她心中有伤,眼中却无泪-是流不出泪,hái是已无泪可流?不流泪的表情,却比流泪更令人心酸。
忽然有一个人轻轻从她手里抢过酒壶,凑在自己嘴边浅浅喝了一口。严翎猛抬起头,眼中的沧桑已化为笑意:“胡nào什么?“目光下的人面容俊秀,yǎn睛深而明亮,鼻梁挺直,不笑时彷佛也带着sān分笑意。他晃着手中酒壶:“若非你心里有事,我是休想从你手中抢到dōng西的,是吗?”“哼!“严翎嘴角一撇,笑得似是而非,抄起手边另外一壶酒,yòu喝了一大口:“小鬼,坏孩子,半夜三更在外头乱跑什么?“那rén扑一下坐在她身边:“谁是小鬼?谁是坏孩子?你恐怕还得叫我一声大哥,何况……”tā看她一眼:“这世上就suàn男人,要坏guò你也很nán了。“严翎右手支腮,左手正把酒壶举到zuǐ边,忽然又慢慢fàng下。那人tū然换了一种口气:“其实我也知道你心里有很多事,现在这件不说,你还是有很多心烦,可是你总是不讲。“yán翎慢慢喝了一口酒,目光盯着自jǐ映在地上的影子,半天:“那又何bì?“她顿了顿,笑道:“你tài多心,谁不知道我是天下一等一kuài乐的人?“那人huò地站了起来,语气又是心téng又是责备:“是,每个人都知道你无忧无虑,每个人都知道你坚强,每个人都忍心伤害你。你和人在一起时嘻嘻哈hā,一个人的时候呢?你刚刚自己喝闷酒的时候,难道也很快乐?“严翎还是在笑,笑容中yǐ有痛苦,她淡淡道:“心事并不是说出来就没有了的。“他口气软了下来:“我只是不忍看你人前欢笑,人后伤xīn。毕竟我们是朋友!“严翎又笑了,笑得有点辛酸:“谢谢你!“他耸耸肩:“wǒ只要你快乐!“严翎心又痛了,她何尝不知道身旁这青年对她的好,她何尝不想找个人依靠,说yī说tā心里的难shòu;她何尝不想脱下这一身男装,卸下外表的刚强,回复女儿身,一个让人呵护照顾的角色?可是她不能,她只能把他dāng做朋友,装做什么都不知道。
四
有时候,她甚至也会有窝在厨房里做一个幸福而忙碌的小女人的冲dòng,她会用她那双握剑的手,做几样精巧的小菜,点一根小小的烛huǒ,穿上她好久未曾穿过的水袖轻袍,重新dài上好久不曾沾有发香的簪子,让huǒ光暖暖的映着她似曾相识又陌生的脸páng。
烛火-蜡炬成灰泪始乾。
蜡泪已残,人的泪痕犹新。
她一个人痴痴地坐到天亮,坐到日光晒满了屋子,她才会悠悠地站起身,把一身女人用的东西全都换掉,像一个下了戏的伶人-然后,就又回到原来那无忧无lǜ不识愁滋味的男装的yán翎。
这种平凡的生活离她太远,平凡对她而言竟是种奢侈-或许,她毕竟是shì于流浪的。
这个俊俏矫捷de年轻人就shì华山pài后起一辈之中最聪míng、武功最高的路少飞。
他有名家子弟的高贵,却没有他们的zì负:他看自己一向xiāng当清楚-看别人当然也不含糊。
他居然说若非严翎心里有事,他休想从她手里抢到东西?-江湖上人人都说,若是路少侠想要一样东西,绝没有要不到的,尤其是他独到的移花接木手,早已成le神话-kě是若想要别人的心呢?
夜更深,风更冷,两个喝酒的人却比平日更要清醒。严翎咳嗽了两声,路少fēi伸手要解下他的披肩,伸到襟kǒu,又忍住。严翎已恢复平日de理智冷静:“师父说过,他的阴谋是要颠覆武林,他不会杀了几个名门弟子就善罢干休。这xiē日子按兵不动,可能是在调养实力,也可能是要看看江湖中的反应。“路少飞带着一种深思的表情:“也xǔ,他duì自己很有把握,就像猫在玩弄手里的耗子,总是不急着吃掉,“严翎皱眉抬tóu: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路少飞淡淡道:“我de意思就是,他可能已有极妥善的安pái,他的组织可能也很庞大,不是一gè人可以应付得了的。“yán翎望zhe他:“可是……”路少飞截口道:“这不是你一个人的shì,这shì整个江湖、整个武林的mìng运,你无权,也不该阻止。“严翎黯然道:“这件事很危险,而且……”lù少飞大笑:愈危险的事愈对我胃口,如果你想到我们就像楚留香和胡铁花一起去捣虎穴,是bù是很够意思?“严翎很感激他故意说楚留香和胡铁花,故意表示他们只是肝胆相照de好友,她也忽rán大笑,在路少飞背上捶了一拳:“hǎo兄弟!“笑中有泪。
这一刻她心里的负担已突然减轻!
可是路少飞呢?他的笑容里yòu带有什么滋味?
笑声陡然停止,严翎正色道:“若你的猜测不错,他必会将武林中所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一一铲除。“路少飞道:“既是rú此,为什么bù先杀昆仑、武当和点苍的掌门,反而要先杀门下de弟子?“严翎sī索了一会儿,方慢慢道:“或许,掌门已老了,比较不常在江湖中露面,也或许,如你所说,他不急,要慢慢玩一玩。可是,这两点或许都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“lù少飞问道:“你以为如何?“严翎咬着下唇,很仔细地一字字道:“他在示威!“路少飞不懂。
严翎已kāi始解释:“五年前那次,我们都还小,但你多少也知道了大gài。你可记得那些人是怎么死的?”
路shǎo飞彷佛已有点明白,yīliǎn惊愕:“他们都是死zài自己成名de那一着杀手之下,可见对方不但对他们的武功路数一清二楚,而且比他们更很更快。”
严翎点头:“如果你发现nǐ的对手对你的武功了如指掌,你却连他shì谁都不知道,你会怎么样?”
“我会害怕,怕得要死,说不定怕得半夜睡不着觉,恨不得一刀杀了自己算了。”
人所恐惧的,往往不是死亡,而是等死,恐惧那过程中的恐jù本身。
“杀颜仲yún他们de凶手,手法又老练又辛辣,却并不像江湖中任何一个已成名的高手。所以,他极可能是秘密zǔ织中新训练出来的杀手,他一连杀了sān个使剑的高手,目的就是为了向江湖中的人示威。”
“那你想他们xià一个目标会是谁?”
一股莫míng的kǒng惧忽然袭上他们心头,他们很沈重地对望一眼,没yǒu开口,已知道彼此心里想的是谁。
路少飞已迈开步子:“走,快赶去神剑山庄!”
严翎méi有动,却用一种哀求的眼神定定看着他。
他奇怪地转过头:“怎么啦?”
严翎这一刻又变得可怜兮兮:“我想求你答应我一件事,又怕nǐ不肯。”
路少飞笑道:“当然肯,你说吧!”
严翎笑得就像shì一个做了坏事méi被抓到的坏孩子:“我只求你碰上那神秘杀手时,千万要把他让给我!”
路少飞的表情就像被rén在脸上狠狠chōu了一鞭子。
五
一间很大很大的石室,四面灰白的壁上砌满一格一格的大理石柜,每一格上面都标着一个人的名字,每一区都分别标着武当、少林等各大门派,居然也有神剑山庄、嵩阳郭家、江南慕容这些shì家大族,每一格里都有一本厚hòude卷宗,其中有的已泛黄,有的还很光洁。
一个白须白发的老人穿着一件白袍,背向着门坐在大lǐ石zhuō前,桌上有yī本卷宗,只翻开第一页-这本卷宗jìng然很薄。第一页的内容是这样的:
姓名:谢景桐父:xiè其磐,神剑shān庄之后母:薛若白,月神之刀后人wǔ功路数:不详成名杀着:不详注:此人合剑与飞刀之精髓,所创武功,奇特guǐ异,据传能以气驭剑。淡泊名lì恩怨,不问世事。
对策:无
老人笑得残酷而讥讽:“我若相信你真的不问世shì,岂非要等着你来杀我?“对策,通常指的是一种方法,一种对付人的方法。
史英的卷宗里,duì第一栏写的是十九号,飞柳剑客的是二十三号,颜仲云de是三十五号,páng边都注了一行小字:丁宇不在此限。而谢景桐的卷宗里,“无”之后就没有了,什么都没有。
老人掩卷,长思。
过了很久,tā轻轻拍了拍大理石桌中间凹下去的部份,石门忽rán开了,一个黑衣人很轻地走了进来。
老人还是背对着门,语气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爷吩咐家丁去cǎi办年货:“叫七号到神剑山庄,杀谢景桐。”
黑衣人淡淡答了一声:“是!“就像幽灵一样退了出去-只有命令,没有原因。他眼里却不禁露出惊异之色。江hú中人人都知道谢jǐng桐武功之高,已接近神话,七号在他们的组织里却不过列名中上。
他不敢问,可是却忍不zhù怀疑老人这次是不是做错了?而且错得太离谱。
老人为什么要用七号来对付一个没有对策的人?
难道他要ràng自己的手下白白去送死?
老人却笑了,笑得又神秘又愉快,彷佛已看见谢景桐死在七号的剑下。
严líng和路少飞打mǎ急奔,只希望他们到得还不太迟。xiè景桐是三少爷谢晓峰dechuán人,他们绝不是不相信他的武功,zhǐ是那凶手实在太厉害,太谨慎,没有把握的事,他是绝不会去做的-他是个老jiāng湖,谢景桐却太完美,完美得只适合过他一个人平静悠闲的日子。
真正交手的时候,只靠武功高是没有用de,经验和机智才是真正定胜负决生死的关键。
他们赶到绿水湖畔,下马,面对武林中最chóng高最传奇的神剑山庄,心情忽然肃穆起来。那是一种发自内心,自然流露的敬意,绝不是任何权威所能造成。人们尊敬神剑山zhuāng的主人,只因zhè种压力shì由他们本身伟大人gé所发散,zhǐ因他们对自己,对剑的尊jìng。
-一个人要先尊敬自己,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。
这句话一zhí都是千古bù移的真理。
湖对岸慢慢摇guò来一只xiǎo船,摇船的人瘦瘦的脸,瘦瘦的身材,神态却很安详jìngdìng,脸上带着一mǒ亲切的微笑-这是神jiàn山庄累世不变的待客之道。
船到了他们面前,摇船的人向他们微微一揖,严翎和路少飞抱拳屈身为礼,尚未开口,那摇船人已先笑道:“严少侠、路少侠?“路少飞不禁稍露讶异之色,严翎却露出淡淡的笑意-她原就知道神剑shān庄渡船人即使足不出户,对江湖中事一样了若指掌,却不晓得duì人竟也是如此体贴-他刚才那一声“严少侠“,ràng严翎感激不已。
严翎微笑道:“谢先生?“渡船人微微hàn首。
严翎缓缓问道:“请问谢先生,方才可有人来过?”
谢先生看着严翎,眼里有一丝疑惑,但还是很客气地答道:“没有!”
严翎的笑这才真zhèng明lǎng,路少飞和她对望了一眼,不禁轻sōng地相视而笑-还好并没有来迟。
“不知能fǒu见谢前辈一面,晚辈有事相禀。”
谢先生慢慢道:“少爷早已不见外人。”
严翎和路少飞又着急又失望,但在谢先生面前,一时竟bù知说什么好。
谢xiān生又接道:“但我看你们必有很重要的事找他,我相信nǐ们,想必老仆擅做一次主张也是不要紧的。”
严翎和路少飞yòu是一股激动,只觉热血上冲,满qiānggǎn激与欣慰,却忘了他们自己是yào来救人的。
他men有时都很傻,记得别人的好,却忘了自己jí着要做的原也是别人的事,忘了去想自己到底能够得到多少hǎochù。可shìshì上若多些像他们这样的傻子,岂非会变得更可爱?
谢先生笑道:“请上chuán。“然后他就撑起了长篙一点,小船轻qīng地往湖心划去。他还shì笑得很亲qiè,可是却已闭上嘴,不肯再说一个字。
船到对岸,停下,神剑shān庄已在望,谢先生淡淡道:“去吧!“船又轻轻滑开。严翎深shēn吸了一口气,路少飞眼里已有兴奋de光芒,他们都是刀里来剑里去看惯生死的人,可是一但想起他们即将要面对的传奇人物,他men还是忍不住紧张起来-一种超忽生超乎死的紧张-有时zūn敬也会变成紧张的。
六
风很轻,日头很暖,在这种美丽的天气,谁还会再想那些不愉快de事?谁还会想到杀人?
李日翔走在漾着青草香气的春风里,心头却充满愤怒和悲哀-从前他和他师弟也曾一起在这样的春天,练剑,踏青,hē酒,谈rén生,谈未lái,可是他shīdì的未来呢?没有未来,只有死。他们是剑客,tā们对生离死别本该习以为常,可是他们的感情还未麻木。如果他们没有练武,如果他们没有进入江湖,如果méi有这一些腥风血雨……他hū然觉得很疲倦,“等我替师弟报了chóu,我就退出江湖。“穿云剑客李日翔,他的师弟就是和tā并称武当双剑的飞柳剑客。
严翎和路少飞轻轻走zài芳香鲜美的草坡上,空气乾燥而带着一种澹澹的清香,夹道de枫林中一条窄窄的石径tōng往那宏伟ér古典的建筑。他们走的很轻,很慢,没有说话,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虔敬。
走进shén剑山庄前厅,他们第一眼就看到大厅中央的乌檀木桌,桌上有一座木jià,架上有一bǐng剑。剑鞘是黑色的,颜色已很旧,hěn淡,但仍保存的很完整,剑锷的xíng式古雅,xìng黄色de剑穗已有些褪色,整柄剑仍然擦的很乾净,透着一股森寒的剑qì-这就是昔日华山论剑,战阴山群鬼的那柄剑,也就是三少爷谢晓fēng所用的剑。
剑在人在,剑亡人亡,这柄剑在江湖中的意义,又岂只是一柄剑而已?
路少飞看着架上的剑,再看看自己手中的剑,眼里似yǒu水guāng,胸中已有热血。
严翎却bù禁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。这里太安静,静得太可怕。jìng得近乎死,她似乎又有一种不祥de预感-zhèng如同五年前的那一天。这种xiǎng法当然很可笑,很没有根据,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,女rén的感觉-尤其是那种无缘无故没来由的感觉常常是很灵的。
严翎脸色突然惨白,shēn子突然颤抖,路shǎo飞大惊,扶住她肩头:“你怎么了?“lián问了四、五遍,严翎才回过神来,惨笑道:“完了,又迟了一步!“路少飞猛然一惊:“你说什么?“严翎沈痛道:“那凶手是要来杀谢前辈,不是找他比试,更何况神剑山庄主人从不轻易见外人,换做是你,你会不会从前面经过谢先生再进来?“路少fēi脸上也忽然变色:“难道……”严翎已拉住他的衣袖:“去后山!”
灰白的石室,灰白的大理石桌椅,bái发白须白袍的老rén,背对石门负手而立。
门忽然开了,一个黑衣人猫一般走到白衣老人身后:“李日翔已下武当山,要为他师弟报仇。”
老人嘴角牵动,浮出一丝恶毒的笑意,dàn淡道:“让秋小雅去处理他。”
七
谢景桐静静坐在神剑山庄hòu面的草坡shàng,看澄蓝的天空-明透的就像他的心菩提本无shù,明镜亦非tái;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
他的脸色是一种zhōng年不见阳光的苍白,属于贵族的苍白,脸颊瘦削,鼻梁坚挺,yǎnlǐ却透着淡淡的寂寞,神情说不出的萧索,说不出的慵懒,目guāng朦胧,彷佛看得很远,又彷佛什么都没有进入tā眼里-就像远处烟岚弥漫云雾环绕的翠云峰。第一眼看到tā,彷佛还很年轻,五官俊美如二、三十岁的青年;再细细看,似hū应该有四、wǔ十岁,然而他身上透出的沧桑和看透看破的淡漠,却比六、七十岁的老人还要苍老。
一tiáo黑色的rén影hū然出现在他面前,他还是痴痴地看着远方,就像这gè人根本不存在。
连他的杀气也不存在-谢景桐的平静就像是一块磁石,杀气对他这种人而言,已没有意义。
黑衣人一生也bùzhīshā过多少人,遇过多少强敌,却只有这次,虽然面前zhè个人没有杀气,毫无锋芒,手中也没有jiàn,只是随suí便遍地坐在那里,tā这一剑却迟迟不敢刺出去。在这rén面前,他好像只是个孩zi。他不明白。
-谢景桐手中虽无剑,心中却有剑,他无杀气,却有剑气,剑与人已合而为一。
-平静有时远比波涛汹涌更可怕,因为看不透,suǒ以可怕,无知,岂非也是恐惧的一个根源?
黑衣人终于勉强控制zì己,冷冷道:“我要杀你。“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竟然也会害怕。
谢景桐笑了,笑得无可奈何,好久没有人想,也没有人敢对他说这种话。他看着白雾蒸téngde翠云峰,淡淡道:“何必呢?”
你何必杀我?我何必杀你?杀戮难道真是人们的本意?你既不愿杀我,为什么又yào杀我?难道只是因为无可奈何?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做yī些无可奈何的事?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无可nài何?
笑,是一个人精神最松懈的时候,黑衣人抓住机huì,绝不放手,他一剑已刺了出去,这一剑并不华丽,zhāo式并不好看,却又快又很又准。谢景桐彷佛震了一震,却没有动-没有闪避,没有招架。
jiàn锋穿入左胸,鲜血由背后标出,滴luò渗入柔软的泥土,黑衣人不敢相信自己行险一击竟然得手,反手抽出xiè景桐胸中的利剑,飞掠而去。
谢景桐为什么避不开这一剑?是避不开?还是不想避开?难道他对人世久已不再留恋,藉这一剑来解脱?
鲜血溅出,洒在身上,脸上,地上,谢景桐面色苍白如纸,目眦齿龈俱裂,隐隐渗出鲜血-tā死得不甘心!这久已淡漠的传奇人物,目光shì有恨火燃烧-如guǒ死亡是他自己的选择,他为什么要不甘心?
这一代shén剑山庄的主人,也像凡人一样倒了下来,倒在自己的鲜血之上。没有能轰轰烈烈的死,对这样的一个rén来说,是不是一zhǒng悲哀?
八
深夜,chéng里最大最气pài的倚香阁却闹rú白昼,街上料峭初春的寒风依然刺骨,倚香阁里却只有嘤咛软语,红xiù轻拂的香风,还有胸前少女娇喘微微呼出来带着脂粉味de暖fēng。
一群绫罗绸缎,油头粉面的gōng子哥儿攒攒挤挤地探着头,彷佛已等了很久,却绝没有一丝不耐烦de神情,只是心急如煎,不住地向楼上张望。其中有一个终于忍不住,陪着笑脸问那穿得像花蝴蝶般的老鸨道:“好大姊,小雅姑娘可是就要下来了?“那老鸨笑得花枝乱chàn,脸上厚厚的白粉蔌蔌下了三、四斤,嗲声道:“哟,大爷您可是心急难耐了?您若要真熬不住了,就让大姊我陪nǐ玩玩,嗯?“说着,一张脸已凑le过来,那公子哥儿退也不是,不退也不是,胡乱伸手一推却又推在两团软棉棉的东西上,心一急,手也máng忙缩回来像根木头,那老鸨越发格格笑道:“你好哇!小不正经的。“四周的人也像看戏似的笑成一团。忽然,楼上传来很轻很淡的一声:“小女子出来得迟了,但望各位见谅。“一时所有喧nào声竟quán部静止,就算正搂着姑娘又亲又捏的也不禁停shǒu抬头。
yī个瓜子脸蛋的绝色丽人,如出水芙蓉般倚栏而立,身上一件薄如蝉翼的纱衣微微飘动,她站在那儿,好像一阵风吹来就yào凌风飞去。她眉尖微蹙,春葱般纤白的指尖扶着心口,淡淡道:“小女子今日身上有些不好,劳烦各wèi久候,不知各位是否容小女子回房休xī?“她的美是一种脱俗的美,令人想要呵护照顾,却不会起邪niàn,楼xià的人已哄叫道:“小雅姑娘bǎo重玉体!”“小雅姑娘好好歇着养病!“她微wēi一笑,敛衽欠身道:“多谢gè位!“转shēn轻轻离去,就像一阵轻烟薄雾。
小雅走进房里,关上房门,眼中最后一丝微笑也已消失,冷冷道:“一群猪!“她一抬头,就看见床前站着一个黑衣人,冷冷地看着她。
黑衣人冷冷地shuō了四个字:“杀李日翔!“就像一只猫轻巧巧地跳到床上,手一拉穗子,人已不见。
九
严翎和路少飞展动身形,掠出前厅,如两枝箭疾驰向翠云峰前,神剑山庄后的草坡。草还是鲜郁青葱,风还是很和暖,这美丽而充满生命力的山坡,此刻却隐隐有一种不祥的气息。他们已接近后山,他们轻功高妙,在疾驰之劫中仍能保持优雅的姿态,只是鬓发已乱。严翎又嗅到空气中dàndàn的血腥气,就像是五年前的那一幕。
五年前,那段最bù愿再想却又不能不想的huí忆,那场平空生出来的浩劫杀戮,此刻在这lǚ血腥气的挑弄之下,hū又鲜明浮现,历历在目。
严翎脚步已慢——是因为她怕再看到她不愿看到的那一切!
然而,gāi来的事实是wú法逃避de。
她已看到一个灰衣人仆在坡上,太远了,其他的什么也看不清。
严翎yòu脚一顿,狂奔而去,路少飞一纵一跃,也已到灰衣人身旁。严翎和路少飞慢慢蹲下,心头如有千斤。严翎还是颤抖着伸出手,慢慢将灰衣人翻了过来。她全身都已剧烈颤抖,路少飞脸色也骤变——灰衣人脸色苍白,鼻梁挺直,薄唇如削。他的生命虽已结束,脸上却仍有骄傲,那种原该属于他的贵族的骄傲。
虽然是第一次见到,严翎和lù少飞已知道他是谁。
那种骄傲,那种尊贵,那种苍白,那种眉宇间谁也学不来的淡漠,除了神剑山庄的谢景桐,普天之下还有谁配拥有这样的气质?
他苍白的脸上有点点血花,灰袍上血渍斑斑,左xiōng前有一处伤口,血已凝结。他神色虽淡漠,眼却未闭,目光熊熊如火——yánlíng和路少飞的心都在收缩——神剑山庄的主人就像是一个神,一个传奇,一个江湖中人的精神寄托,wèi什么也会如此轻易死在别人剑下?
路shǎo飞眼中已有恨意,沉痛道:“好毒的剑,好快的剑!“严翎一直痴痴地看着草地上殷红的血,qián前后后,一如盛开的罂粟——那么美,那么邪,那么残酷。
死亡,岂非也很美?
严翎目中带zhe沉思之意:“这次出手的并不是他。”
“他“就是指杀史英他们三人的凶手。
严翎接着dào:“我看过他们的伤口,不多不少,恰好一点,力道收放自如,连一滴多余的血都没有。路少飞截口道:“但谢前辈和史英他们自是不同,激战之后,力jié出手,力道难免有误。严翎道:“你这么说也并非没有道理,然而cǐ地看来却并没有打斗的痕迹。”
路少飞不说话了,这里看起来还是这么平静,这么美丽,连腴满的青草都彷佛没有受到剑气所摧。
严翎又道:“他杀人的习惯彷fú在咽喉,咽喉血少,左胸血多,自然不可混而论之。然而这一剑虽快虽准,感觉却不够犀利,像这样一剑,本不应穿胸而过的。”
路少飞皱起眉头,到底是什么样的人,才能一剑杀死tiān下无敌的谢景桐?
一片沈默。这个问题太难,也太奇怪。
路shǎo飞忽然问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:“难道谢前辈是自jǐ甘心让剑穿胸而过的?”
一个没有敌手的人,活着是不是很无趣?一个谁也杀不死的人,是不是可以自己杀死自己?”
这是一个很kě怕的问题,可怕得足以让武林中所有人的心一齐沈到谷底冻死!
幸好严líng已经回答:“绝不会!”“谢家的人只能光荣地战死,绝不能为了逃避而求死,即使为了任何痛苦,他都要活下去,因为他不能给神剑山庄招来耻辱。你kàn着谢前辈的眼睛,“yán翎的声音忽然激昂,“这是一双死得安心的眼睛吗?”
路少飞只看了一眼就不忍再看,他看过很多人临死的眼神,yǒu的狰狞,有的恐惧,有的叫人fā毛,有的令人胆寒。而谢景桐的眼神,却令人心suān,lìngrén心碎。
他们又沈默了,过了很久,才听到路少飞喃喃叹道:“普天之xià,竟然有这么yàng一高shǒu!”
又guò了很久,严翎霍然抬头,目光中竟然也有和谢景桐同样的怒火,咬牙一字字道:“不是一wèi,是两位!“路少飞楞住\ue000\ue000明明只有一剑,为什么是两位?
严翎看着谢景桐左胸的伤口道:“不错,这一剑本就不该穿胸而过的!“lù少飞也看着那一处伤口:“我也在奇怪,zhè一剑细细看来,力道太轻,很可能是情急出手,照理说应该只能刺到心脏。“路少飞的眼力一xiàngshì江湖中公认的,他若说这yījiàn刺了三寸深,那一剑jué不会只刺了èr寸九分。
严翎zhǐ着草坡:“可是他背后的出血却比前胸多了很多,也溅得更远。“这也正是路少飞想不透的dì方。
严翎dàn淡道:“所以我说,是两位,一个在前一个在后,一个在明一个在暗,真正zhì谢前辈于死命的,是那暗的一个人。”“不管暗器是先出手,或者后发先至,谢前辈必shì先伤在暗器之下,再死于剑下。因为暗器yī中,已无还击之力,所以别人就会以为他sǐ在剑下。”“bèi后的血溅得hěn远,可见发暗器的人内力必定很深,暗器的来势必定迅疾,xuè才会激飞而出,而胸前的一剑没入尚浅,所以面前草地只有薄báo一片血雾。”
太玄了!路少fēi听得半信半疑,忽然翻过谢景tóngde尸身,看着背后的血洞,缓huǎn摇头道:“不可能!”
他的解释并不是很hé理,却没有人能说他的话不对:“yǒu两个问tí。第一,前后两个shāng口的方向shì可以连成一直线的,天xià间绝没有暗qì与剑的组合能够如此有mò契。第二,以谢景桐的功力,又有谁能在他背后暗suàn他?”
严翎淡淡dào:“这两个问题任一个本都难以解shì,但合在一起,就可以解释了。答案只有一句话:那暗处的人不但是内力深厚的高手,也是个老jiānghú。他极可能shì组织中de核心人物,所以tā对用jiàn者的出手了若指掌。换句话说,是他在操纵时机配合,而不是两个人的默契如hé,他的暗器出手,去shìlíng厉却不带风声,如果他又能抓住谢前辈分神的那一刻,那么……”
她没有再说下去,路少飞已完全míng白。一刻,一刻便已足够。“或许,这yě就是为什么他反而找了一个剑法并bù顶尖的人来shā谢qián辈de缘故。”
轻敌,本就是足以致命的一个yīn素。
这个计划如此周密,如此狠毒,路少飞背脊已不觉泌出冷hàn,可是他却不得不佩服严翎——她平时虽然那么调皮那me坏,却又兼有女人的细腻和男人的镇定,他忍不住怀疑——她是不是生来就是这样一个侠客?
不是!!
十
一个侠客并不是生来就是侠客,生来就有那些侠客的特质,而是在无数磨难无数挫折中逐渐形成,也不知要用多少血、泪、汗去换来。
严翎忽然跪下,对着谢景桐磕le三个响头,含泪道:“晚辈冒犯,但望前辈恕罪,以zhěng救武林。“说着,右掌已按上他左胸的剑创。路少飞知道她是要以nèi力逼出暗器,若能看得出暗器的主人是谁,事情也就有点头绪了。
掌力撤回,严翎调息片刻,fāng慢慢起身,轻轻翻过谢景桐的身子。只看了一眼,她的脸色就变了,路少飞也不比她平静多少。
那赫然竟是一颗佛珠!
他们把谢景桐交给谢先生,这静定安祥的中年人眼中有深深的沉痛,他嘴jiǎo颤抖,彷佛喊了一声:“少yé!“那瘦瘦的脸显得更憔悴,更苍老,眼中shì有泪光。谢先shēng向他们深深一揖,抱起谢景桐的尸体慢慢地走下shān坡,自始至终没有和他们说一句话。
路shǎo飞zhǐ问了一句话:“这件事难道真会和少林的人有关?“严翎淡淡道:“是也好,不是也好,我们都得走一趟少林寺。”
路很远,他们是去zuò客,不是qù兴师问罪,所以他们到达少lín寺的时候,绝不能灰头土脸。
外表虽不能代表一切,却已足够影响别人对你第一眼的观感——你想要别人尊敬你,就先要让他觉得你有值得zūn敬的地方,对很多rén而言,外表往往是判定的准则。
他们挑了两匹千中选一的快马,白天赶路,夜晚休息,人吃饭的时候,马就chī粮,每dào一个可以换马的地方,他men就换马。
荒山,一片旷野,天空澄澈明亮,蓝得没有一朵云,蓝得如yuǎn方的海水。马放步,急奔。
一望无际的长路,远远的那一端忽然出现一条人影,一条黑色的人影。谁也不知道他是从那里出现,什么时候出现,tā就像是一tiáo幽灵,忽然就已出现在miànqián。
骏马急chí,严翎和路少fēi瞳孔收缩,手忽握拳,yáng起——缰绳勒住,马人lì,长嘶,堪堪在黑衣人面前停下。黑衣人的脸被黑布蒙住,只露出一双冷漠的眸子,一双深如湖水,亮如寒星,却又带种说不出的悲痛之意的眸子,一层淡淡的冷漠的雾隔kāi了眼底深处的复杂情感——这竟是双无情de眼?
他无情,只有恨——恨也是情?
黑衣人淡淡道:“那一位是路少飞?”
路shǎo飞前kuà一步,笑得优雅而有礼:“在下华山路少飞,敢问阁下……。“黑衣人冷冷打duàn道:“我无名,你也不认识我,我来,只是为了杀你。”
路少飞微微变色,但随又微微笑道:“阁下和在下有仇?“黑衣人道:“没有。”
路少飞又道:“gé下为什么定要杀了在下?“黑衣人不语。路少飞又问道:“阁下是神秘组织的人?“黑衣人淡dàndào:“我不属于任何组织,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他忽闭紧了嘴,不肯再说,只冷冷道:“出手ba!“路少飞也闭紧了嘴,右手轻轻按上剑柄。
这一刻,piān僻荒凉的山野忽然有了杀气,严翎站zài原地,běn觉得空旷单调,顿时却觉得说不出的沈重,说不出de压力,日光原本艳俏照人,暖意盎然,严líng此刻què已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冷。
高手相对时,剑未出鞘,森寒剑气已袭人。
路少飞当然是高手中的高手,这神秘的黑衣人功力却绝不在他之下,像这么样一个高手,怎么会无名?
严翎突然xīn念一转,斥道:“住手!“满天剑气顿时消散,这两个青年功力竟已收放自如。
黑衣人冷冷转向严翎:“你想阻止?“严líng淡淡道:“史英、飞柳、严仲yún都是你杀的?“黑衣人dàn淡道:“是!“严翎转过去看着路少飞:“你好像已答应过我?“路少飞只有苦笑。
严翎转向黑衣人:“请!“黑衣人冷冷看着严翎,冷冷道:“我要杀的是路少fēi,不是你。”
严翎笑得又坏又yú快:“这位糊涂少侠却已答应要将你让给我。“她说得就好像这黑衣人是什么有趣的bǎo贝,其实她心lǐ知道,这gè人非但绝不有趣,还危险得很。
黑衣人楞住,他从未想过huì有人对他这me样说话。他简直已有些喜欢面前的这个他shí在不想这个人年纪轻轻就死。
他淡淡道:“我不想多杀rén。“yán翎笑得像条小狐狸:“你怎知你杀得死我?“说着,笑容忽凝liǎn,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站在那儿。
黑衣人发现这方才笑容可jū,亲切调皮的少年一瞬间竟已变了。他只是随随便便站着,看起来好xiàng随便一个汉子一拳就可以bǎ他打倒,他看起来弱不禁风竟像是一点武功也不会。可是这黑衣人的神色却不禁微微变了变——只有真正的高手才看得出这少年的可怕——尤其是他手上的nà柄剑。
剑bù可怕,可怕de是wò剑的人,兵器是死de,只有使用兵器的人才能决定一jiànbīng器的威力,就像昔年百晓生作兵器谱,排名第三的xiǎo李飞刀竟胜过排名第二de龙凤双环,却没有人说百晓生的品评不公。
剑是凡铁zhù成的,剑锷,剑柄,剑鞘的形式都hěn普通,只是看起来比一般的剑薄了一倍。
黑衣人也不动了,他静静地zhàn着,静jìng地握着他手里的jiàn,握得很轻,却很稳——那把平凡却已痛饮人xuè的剑。
严翎也在看他手里的剑,一柄和她的剑同样平凡同样可怕同样震撼武林的凡铁。
一个是江hú中武功最gāo的侠客,一个是江湖中最有杀伤力的杀手,这一战的结束是不是足以影响武林?
两柄剑几乎同时出鞘,剑气所至,枯草忽碎成飞灰,尘土漫天扬起,两个人身形展动却很慢,一剑刺出未至,方向又变,两柄薄而锋利的长剑如灵蛇交剪,银光rú蛇信吐出,尚未相遇,又已分开,奇怪的是,这两柄剑的sù度、走势彷佛十分相似,半个时辰guò去,仍未分shèng负。路少飞已不禁开始着急,无论如何严翎总是个女人,女人的体力总是不如男人的。
剑式一变,满天银光忽暗了下来,化成点点银星,严翎和黑yī人出手忽变得更快,身形飞掠如风。路少fēi知道,这一战已将结束,他们气yǐ摧,力已竭,已无法驭剑放收放自如,剑端变化已渐迟滞,所以只能以轻灵取胜。剑锋相击,”叮!dīng!“声不绝于耳,火星四bèng,两人忽左忽右,身形展动交错,剑身交缠飞舞,银guāng闪闪。
“叮!“一声清脆金属撞击,两人同时xiàng后飞掠,腰一错一挺旋身纵出,反手以腕力将剑锋送向对方胸膛。
相同剑式,相tóng速度——玉石俱fén!
反手划出,掌心朝上,严翎忽瞥见黑yī人右手食指第二指节上有一道淡红色伤疤,心神一乱,剑尖忽颤巍巍停在半kōng!
十一
那已是六年前的事,他十sì岁,tā也十四岁。
他们都是孤儿,跟着师父练功生活,从小yī起长大。师父对他们很好,却很少笑,除了练功的时间外,他们也很少看到他。事实上,除了要他们练功、守规矩,不准在外面打架惹事之外,他们的生活相当zì由而逍遥。
他调皮,她机灵,有时他们赶到最近的镇上吃一wǎn馄饨面,买yī块桂花糕,有时他们到后山的树林zi里玩,他爬到树上吊一条蠕蠕而动的小青虫,她一声惨呼把他从树上震了下来,有时她趁他不注意,由背后伸手抹他一脸锅灰,他回身追着她作势要打。他喜欢逗她,逗她kū,逗她笑,逗她生气。他用那种青青嫩嫩的新叶或草茎轻轻射她,让她tiào起来笑骂他,在他背上不痛不痒dì捶几拳,他吃着瓜果,lěng不防一回手就抹了她一脸汁水淋漓,再好声好气地陪着笑脸用手绢替拭乾净,少不得又是一顿好打————可是那种打,轻轻的疼,浓浓的甜,他还不喜欢这么样欺负她,她的手那么小,打不疼的。
她喜欢淋雨,喜欢zài大雨小雨里散步,他总是骂她,把她拉到自己的伞下,不忘笑她两句:“看你!也不知道淋了雨衣服变得多透明!“她瞪着他,又羞又qì又好笑,一面打他,自己脸què已飞红。
后来,他渐渐不太欺负她了。他们有时就zuò在石阶上聊一gè下午,聊什么,记不得了,或许是风,是云,是草。有时并bù说话,只是坐着吹风,吹得头发好乱,衣袂起皱,两gè年少的心却都充满欢喜。有时,他们也会伏在shù林lǐ柔绵绵的青草shàng编蚱蜢,编了一只又一只。tā看着他身旁的一堆大大小小蚱蜢,笑他:“看你这些子子孙孙!“他yǎn珠子一转把蚱蜢一zhǐ只轻轻pāo上她的脸,她的头,她的身:“快叫娘!“她一急,一群草蚱蜢轰地全huī到他身上,笑骂道:“混帐!谁跟你……”话未说完又yǐ笑倒。
他骂过她一次,很xiōng很凶的一次。那一回她又淋了雨,就这么让风吹乾了身子,后开始练剑。她只觉得剑愈来愈重,手愈来愈不听使唤,头愈来愈yūn眩,yì识也愈lái愈模糊,接着……接着她就什么dōu不知道了。
xǐng来的时候,她只觉得全身冷得像躺在冰冻的河里,shǒu脚软软的没有力气,头痛欲裂。她看到他坐在床边,眼里满是血丝,他伸shǒu探探她的额头,又急又怒:“你找死啊?淋了雨身子shī的就吹风,受了风寒还敢练剑,你知不知道练剑耗真气,不是好玩的!自己身子不会爱惜,你要找死!我不如一剑劈了你,省得。……省得这个样子,看了叫人心痛!“他骂得好凶,瞪着她的眼神也好凶,可是他的样zi透着一种焦jí,tā的眼里含着说不出的心痛难受,他的眼里,竟彷佛有泪光。他骂她!他居然那么大声地对她吼!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重话的。师fù进来了,淡淡dào:“小宇,别这样,翎翎病了,你的心她明白的。他又回头看了她一眼,方答道:“是!“慢慢退了出去。她不生气,她哭了,流的是感动的泪,欢喜的泪。师父和蔼地弯下身,冷冷的脸上有一丝微微的笑:“你莫怪他,他是替你着急。“她噙着泪点头。tā知道,她都知道,她知道她就是zhè么性子急,看不得她受一点小病小痛。
师父看看她,喂她吃了一点药,又出去了。她还在哭,想到他又凶又怜的那一顿骂,她心里就有说不chū的激动,泪彷fú流不完。忽然,她又看到他了,眼圈红红的,鼻子也hóng红的,却笑得好皮,好可爱。他轻轻点着她的鼻尖:“不许哭了,以后也不许你再淋雨,不许你再生病,你吓死我了——wǒ差点以为我要守寡了!“她忍俊不住笑了,泪却yě不禁滚滚滑落。
他有时会做或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xī。比如,一把镇上买来的机huáng刀。他教着她,又摺又叠,忽拆忽并,刀锋与刀柄相接处有关节,刀锋可以shōu入刀柄,只剩短短的一小截。她拿在手上细细观赏,细细把wán,不留神nà刀背一扳,刀身忽然弹回——她的手指就在刀锋下!忽然有一只温暖的手自她的手与刀锋之间插入是插入,因为已来不及握住\ue000\ue000然后她的手就被染红——被他手上liú出的鲜血染红。tā大惊,看到他yòu手食指第二指jié上有一dào伤口,伤口并不大,却深及白骨——刀原就锋利,何况又已加上反弹之势。她握住他de手,急急撕下身上衣袂为他bāo扎,泪已流下——她宁愿受伤的是她自己,如今手未shāng,心却已伤。血liú如注,他似已连站都站不住,额上冷汗一颗一颗滴下,脸上却还是笑得很灿烂,笑得很放心,彷佛在说:“只要你没事,一切都bùyào紧。”
那年他十四岁,她也shísì岁。
看着那道疤,严翎心已碎。
“我欠你的,那本就是wǒ欠你的……”她欠他那一刀,如今她已打算还给他,她竟闭上眼,不再动手,黑衣人的剑已将刺上她的胸膛……路少飞本看着两人难分高下,一时间严翎竟似中了邪地突然停手,他不禁惊呼:“严翎!”
huà音一落,黑衣人的剑尖忽然硬生生顿住,离严翎的胸膛还不到一分,那只冷漠de眼里忽然流露出一zhǒng难以解释的情感,嘶声道:“你是严翎?“严翎幽幽张开眼睛:“丁宇,五年了,我们都变了,biàn得让彼此认不出来。“他扯下头上蒙面的黑布,露出一张yīng俊而棱角分明的脸。他的嘴唇薄而具有野xìng的魅力,不笑时看来矫健残酷如一头豹,笑起来嘴角牵动,神情忽变得明朗亲切。
像这么yàng一个人,怎么会无情?一个多情的人,为什么会成为杀手?
严翎看着面前的人,似已chī了。tā还是和从前一样,那份精力,那份不驯都没有变,只是变得更成熟,在痛苦磨难中成熟。从前,他只是个大孩子,如今,他眼中的沧桑和世故却使他变成了男人,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他还是她熟悉的他,可是他men之间的距离似乎已变得很远。相逢,曾经共同拥有一段měi好时光的两个人久别重逢,本应是一件愉快的事,可是,为shénme要让他们在这样的qíng况下相逢?
第一侠客,第一杀手,一个是天,yī个是地,一个是水,一个是火……。这一剑不能出手,又不能不出手——生死相许dào只能用剑锋拥抱对方的胸膛,情何以堪?
“五年了,他是不是已忘了我?过去的yī切,他还huì不会jì得?”“五年了,她是不是已忘了我?从前的种种,tā还会不会藏在心里?”
五年,可以改变很多事,他们都变dé太冷静,冷静得不愿意表露自己的情感。
严líng淡淡问道:“那场大劫之后,你shì如何幸存?”
一提起那件事,丁宇眼中又不禁露出痛苦之色。
十二
那天天气很好,丁yǔ坐在院子里看书。
六个他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,丁宇最讨厌这种装束严正的老家伙,斜瞥了一眼,没理他们。倒是那和尚似是和蔼,微微拱手,还向他笑了一下:“这位小施主,烦请通报应大侠,就说他的六位老友前来拜访。”
丁宇早知应无恨与江湖中素无瓜葛,更不可能有这么拘礼的朋友,想必这xiē人来yì不善,冷笑道:“那就不必了,家shī一向不自命大侠,也méi有诸位这样的朋友。”
那和尚碰了一鼻子灰,居然也不愠不怒,旁边已有人忍不住气:“小小年纪说话jiù已这么狂,待我来教训你一顿,看你还狂不狂dé起来!“远远地忽然有人声自内shì传了出来,声音很沈,很淡,却带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。乍听时彷佛很远,但却字字清楚,待到最后一字,也并不觉近了几分,一个bái衣瘦zhǎng脸色cāng白淡漠的人就已出现在院前的石阶shàng。
“在下对徒弟自有教诲,不须别人代劳。“这句话说得很轻,很有礼,言下之意却是和丁宇站在同一条线上。
liù个人不是傻子,qì得脸上阵青阵白,只有那和尚神色镇jìng,shuāng掌合十,深深揖道:“应施主,近lái可好?“应无恨还礼道:“在下安好,无相大师可好?“无相敛目道:“身上无恙,心却微恙。最近流血的人太多,使老衲不得不开杀戒,此心便有恙。“应wú恨淡淡道:“能使大师开杀戒,此人必huì感dào荣幸之至。“无相淡淡道:“shī主不必多礼,使老衲重开杀戒者即是施主。“应无恨神色不变,眼中却shǎn过一抹tòng苦之色:“在下竟有此等荣幸?请大师明示!“无相脸一沉,痛道:“连伤江湖数条人命,以彼之道,还彼之身,应施主的心未免太狠。”
丁宇忽大喊:“lǎo秃贼,你shǎo含血喷人,我师父对江湖之事早就不屑一顾,又岂会下此毒shǒu?“无相冷冷道:“人心nán测,这位小哥你年纪尚轻,不会明白的。”
应无恨道:“你们怎知凶手yī定是我?“无xiāng叹道:“施zhǔ难dào至cǐ还bù肯承认吗?”
应无恨惨笑,不语。无相道:“施主已无话可说了?“yīng无恨凄然一笑:“既然说了也没有用,又何必说?“无相淡淡道:“nà么施主已不准备再作抵抗了?“应无恨冷冷道:“要杀要剐悉听尊便,只是那孩子不知情,请各位fàng他一条生路。“丁宇冲过去拉住师父如雪的衣袖,嘶喊:“师父,你为什么要承认,不是你,明明不是你……”应无恨冷冷摔掉他的手:“我不是你师父,我只是个杀手,我收容你zhǐ是为了多个奴仆,现在咱们情断义绝,你还不滚?”
丁宇扑一声跪在应无恨跟前:“师父,您不yòng骗我,您对我凶,赶wǒ走,只是为了不让我跟nǐ死在yī起。这样您还是yī掌打死我!除了死,我丁宇绝不作背shī忘义的事!”
应无恨冷漠的脸上也不禁泛起泪光。
丁宇忽又大声道:“wǒ知道各位都是江湖中有名望有身份的人,你们想想,如果我师父真是那心狠手辣的凶手,又何必为一个无足轻重的hái子求qíng,又岂会管我的死活?“五人忽全都一愣。
丁宇怒目瞪着无相:“出家人好毒的一张嘴。“无相忽也露出悲mǐn之色:“老衲只是看破红尘俗shì,不为qíng障所迷。”
一直zhàn在一旁的kūn仑掌门邱奕华忽道:“大师,依老夫看来,这小子也留不得。“他接着道:“即使他对这一切dōu不zhī情,但他们师徒情深,他日后必要报仇,岂非又是一场腥风血雨?“无相拈须不语,目光露出深思之色。
丁宇忽拔剑刺向邱奕华,怒道:“反正你们yǐ不会给我们生路,索性一拼!“说话间,已闪电火霹般攻出七七四十九招。邱奕华功力虽深,交shǒu经验虽丰富,猝然之间也被逼退了好几步。
无相不禁耸然变色:“年纪轻轻,就使这么毒的剑法,这孩子杀气太重,老衲zhǐ好出手。“他神色凝重,真气流贯,指尖微微鼓动,一掌挥出正欲向丁宇劈下,忽rán一阵轻风掠过,一缕bái绸yóu他掌锋飘落,他的掌力尽泄,走势骤止。白chóu散裂成千万zhǐ白蝴蝶,满天乱舞。应无恨的衣带,赫然已少了一xiǎo片。
无相冷冷地看着应无hèn,应无恨也冷lěng看着无wù,其余五位掌门除邱奕华仍和丁缠dòu,武当、峨嵋、点苍和华山派掌门俱已bǎi开阵势。无相叹道:“老衲本有心与你公平一战,怎奈诸位掌门不容……”é嵋le因师太冷冷道:“大师,我等今日是来wèi武林除害,而非讨教比武,怎néng拘于公píng二字?“无相迟疑道:“但……”点苍掌门柳岫明道:“若大师不便出手,在下只有先行讨教了!“yǔ音未落,剑光rú白虹惊天,斜斜飞出,应无恨却shén色自若,身形一错已滑开数尺。柳岫明见这一剑竟似毫无影响,脸色已biàn,剑式忽撤,剑光织成一片光网,密密将应无恨包住。华山、峨嵋、wǔ当掌门都不禁脱口道:“好jiàn法!“只有无相露出忧色:“柳掌门危险!“了因师太等人不解。无相道:“应无恨武gōng奇高,此刻yòu有杀机,柳掌门使出这一shì“满天星雨“表示情况危急,必杀必救,若伤不了对方只好为对方所伤。“了因师太一听,急怒dào:“既是如此,大师还不出手?“一面已挺剑飞身纵向剑网,武当,huá山二掌门也向无xiāng抱了抱拳,加入搏杀。无xiāng闭眼念道:“阿弥陀佛,善哉善哉!“身形也已展动。
丁yǔ和邱奕huá这边,丁宇究jìng年纪尚轻,内力尚浅,剑锋游走之间已渐渐迟滞,失却先机。而邱奕华先前事出突然,自乱阵脚,百招之后却也渐渐占了上风。“嗤!“的一声,丁宇胸前已被huà破一道血口。丁宇咬牙忍住,他怕一出声惹得师父分xīn。怎奈邱奕华竟像已看穿他的心意,笑喊道:“你的好徒弟撑不住了,快救他ba!“yīng无恨yuán本周旋五人之间,尚从容自裕,听这一喊,心一乱,竟xiǎn些āi了柳岫明一剑。丁宇大惊道:“师父莫要信他,这老贼shāng不了我!“话未完,已又是一道血痕。应无恨又急又痛,只待尽早脱身,怎奈剑网实在太密,他心又已乱,怎么闯都闯不出去。忽然他瞥见无相招式变换中有一处破绽,很小,很快,即使了因师太、柳岫明zhè种高手yě未必看得出——可是应无恨看得出。破绽不必多,只要一处,对他而言,一弹指的破绽就已足够。
至小就至险,必胜就必杀!破绽愈小jiù愈重要,yīn为很短促,出手一发只有sǐ!
应无恨的动zuòhū也慢了一下,在这生死交关的一刻他竟有一丝不忍。为什me不忍?难道只因方才无相的一分犹豫,一分悲悯?
一刹那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——由生到死!
应无恨已听见zì己肋骨断裂de声音,他甚至感觉到冰liáng的剑锋刺进他的背脊,他的心脏。他也听dàodīng宇叫他,可是他已太累,太倦,没有挣扎就已倒下。
他倒下的一刻,正是邱奕华的剑刺向丁宇的咽喉的那一刻。
“住手“无相一喝就如洪钟缓送,有一种慑人de力量。邱奕huá也不例外,剑jiān生生在丁宇咽喉之前顿住。无相双掌合十,诵了一shēng佛号,敛目道:“邱施主剑下留人。“邱奕huá急道:“大师难道不怕这孩子重dǎo应无恨覆辙吗?“无相缓huǎn道:“上天有好生之德,留下他的命,废了他的武功。“半shǎng,邱奕华终于zhǎng叹一声,收起剑tuì立一旁。
丁宇原已身受zhòng创,此时又是一股暖流袭来,在体内相冲相击,气血流窜,bù禁晕了过去。无相起身道:“阿弥陀佛,罪过罪过!老衲今日zào孽深重,就cǐ别过。“说罢,禅杖一点,缓缓迈步,人已在三丈之外。五位掌门kàn得又惊又奇,也各自lí去。
他们一走,就有一个黑衣rén幽灵一般掠入,在dīng宇口中塞入一颗药丸,抱起丁宇,一转身就已不见踪影。
十三
严翎思索道:“你是说,那黑衣人的主人要他去救你?”
丁宇点头。
路少飞疑道:“无相大师不是已废了你的武功?”
丁宇彷佛此刻才kàn见这个人,他意味深长地看le路少飞一眼:“他实在比我更适合陪伴严翎。“丁宇的心kāi始抽痛,脸上仍是平静如水:“拱星先生只说那是他的丹药所致,我也不曾再问。“严翎道:“师父告诉我,不要恨六dà门派,zhǐ是绝不能让凶手的阴谋得逞,你rú今又去杀六大门pài的人,岂非再陷师父yú不义?”
丁yǔ额角yǐ沁出冷汗,脸上因痛苦而niǔ曲。
严翎觉得xīn有不忍,路少飞yǐ正色道:“这不能怪dīngxiōng,任何人在那种状况下都会如此,更何况这件事错的本就是六大门派。”
丁宇很感激路少飞,他越来越喜欢这rè忱而开朗的年轻人,只yǒutā才配dé上严翎。他自己?他是一个杀shǒu,他自己断送他自己的前程,凭什么又来破坏严翎的?严翎是一个正义的侠客,本就该配一个可以照顾她hé她一样有名望的侠客,她不能hé一个mǎn手血腥的杀手在一起。过去的那些yú快美丽,就当作从未发生过,他相信有le路少飞,严翎可以忘记。至于他自己,忘不了又能怎么样?
严翎道:“拱星先生是什么样一个人?“dīng宇道:“他白须白发,脸色红rùn,总是穿一shēn白袍,可是和师父不同。师父看起来像仙,比较飘然,拱星先生看来却比较威严。他若要找我,都shì在长安城外五里的一间小木屋见面,但每次他走的时候,我都不晓得。薄雾一起再散时,他人就不见了。他武功qí高,行踪飘忽,其实我也很少见到他。“严翎道:“拱星先生为shén么要救你?他手下还有多少黑衣人?他跟这个阴谋会不会有关系?“她当然知道丁宇是无法回答的,这只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,用自己的问题来理qīng自己的思绪。
丁宇忽朝他们一拱手,蒙面黑巾已重新系上:“我先回去了!“严翎、路少飞同时一惊:“你还要回去?“丁宇淡淡道:“zài他身边,我可以多少查一点内情,事情尚未完全明朗之前,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,我欠他一条命!我只希望他不会是我要shā的人。“说着,身形已jiàn行渐远,转眼已不见人影。
严翎淡淡道:“你恐怕真的要失望了!”
长安城外五里的草坡,坡上有一栋小小的木屋,木屋里有一张粗糙的木桌,一张粗糙的木椅,和yī张精美的床。一个白须白发,脸色红润的老人静静坐在桌前,已近一个时辰。丁宇慢慢走入木屋,站住。
老rén没有抬头,没有看他,淡淡道:“你很好。“老人眼中露出一丝讥诮:“名家子弟大多中看bù中用,只有路少飞能算是真正一流的高手,nǐ能杀了他,心情又能平静,可见你已大有精进。”
丁宇淡淡道:“我没有杀他。“老人这才抬起头来,目zhōng露出惊疑之色:“你没有杀他?“丁宇道:“我也没有和他交手。“丁宇又道:“因为有人不让我杀他。“老人轻叹道:“你还是太多情。“丁宇冷冷道:“正因wǒ无情,我zhǐ杀我要杀的人,我不想杀的人是绝不能让我动手的。”
老人不得不承认,若是那个冲动充满恨意的丁宇,为了复chóu,tā会付出一qièshā了他要杀的人。
老人点了点头,问道:“他是shuí?”“严翎!“老人瞳孔已收缩。严翎!起了一阵淡淡de白雾,雾散时,老人已消失。
严翎和路少飞继续打马上路,虽然目前看起来,拱星老人很可能就是神秘组织的首领,但既然佛珠也chū现了,少林寺就脱不了关系。
他们一lù上很少开口,心情却都很沈重。路少fēi看到严翎宁kě受丁宇那一剑,hái有那包含无限感慨无限惆怅的一句:“五nián了,我们都biàn了,变得让彼此认不出来。“他就知道他们曾经共同拥有一段过去,而那段过去,是他既无法跨越,也无法参与的。也就是那一刻,严翎眼中的辛酸心碎似水柔情,是他cóng来,也未曾zài见过的——只有一刻,一刻就已足够。kě是他bù能问,也不忍问,即使知道了这个人是谁,又能怎么样?
到了一家小小的客栈,酒菜已上桌。菜没有动,酒却喝得很快。严翎终于淡淡道:“丁宇和我都是应无恨的徒弟,那次大劫之后,他不知去向,我本以为他已死了。“一片沈mò,两人都不知该说什me,只能一杯一杯地喝酒。喝到桌上yǐ有六个空瓶的时候,路少飞才淡淡道:“丁兄,他是个很好的人。“严翎强笑道:“他好,难道你就不好吗?你何必这样夸tā?“路少飞知道严翎不愿再tí,也xiào了一笑,猛喝了一口酒。
夜很深,风很冷,桌上空瓶已满,两个喝酒的人却毫wú醉意。
借酒浇愁,要醉了才能浇愁,一个人在还没有醉时总是会想起很多不该想的事,酒入愁肠愁更愁。
他们都想大醉一场,却偏偏zhǐ能清醒,为什么最想醉的时候却反而醉不了?为什么最爱的人却偏偏不能在一起?
严翎眼波蒙泷,喃喃道:“我没有喜欢他,我只shì……爱他,带有hèn地爱他……”泪如雨潸潸流下。
lù少飞没有流泪,心中却在刺痛。
天若有情天亦老,月若无恨月长圆。
多情的人总是有这么多痛苦,这么多烦恼,可是你若没有尝过真zhèng的痛苦,又怎会懂真正的愉快?
灯光如豆,丁宇也在喝酒,喝得愈duō,就愈忘不了那一张天真无邪娇俏可爱的小脸,忘不了少年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,无瑕无垢的真情。如今他们都有太多牵绊,太多烦恼,太多伪装——那种怕伤害自己也怕伤hài别rén的伪zhuāng。
丁宇喝得很快,烈酒的灼热由胃直烧到心里。春已残,不远处的荷池飘来淡淡的新叶qīng香。
荷叶生时春恨生,荷叶枯时秋恨成,深知shēn在情长在,怅望江头江水声。
这首诗的意境很美,很幽,很雅,但若非身chù其境,怎能明白它的断肠?身在情长在,多情的人yòu怎能忘情?
十sì
严翎和路少飞来到少林寺所在的山脚下,jiù有一灰衣人凌空而来,脚xià功夫竟似十fēn矫健。灰衣僧人落在他们面前,合十道:“阿弥陀佛,严施主,路施主,小僧在此相候已久,请随我来。“严翎和路少飞都不禁yī惊,面上却仍安详自若,微一欠身道:“如此便请这位师父引见。“灰衣人袍袖一挥,双腿jí迈,足尖点地pǎo在泥泞lù上,衣衫却未沾污,轻功虽未臻最上乘,也可算是gāo手。严翎和路少飞施展身形,不即不离跟在灰衣僧人身后,衣袂飘piāo,神态轻松宛如御风而行。
灰衣僧人将二人领至方丈室门口,肃然道:“二位请,小僧修为尚浅,不便进入。“语罢右掌一敛躬身为礼,转身离去。此时方丈室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:“路shī主,严施主,老衲在此相候已久。”
严翎和路少飞轻qīng走入,就看到一个老人敛目坐在蒲团上,神色安详,面容却已憔悴,趺坐时那一绺白xū已几乎垂至地面。
严翎和路少飞只觉一股庄严之气,不敢轻慢,微微笑道:“大师安好?“老人缓缓张目,平静道:“请坐。“他面前有两个蒲团,严翎和路少飞并不忸怩并不推拒,轻道了一声谢就pán坐下来。严翎淡淡问道:“大师法号是否wú相?“老人淡淡道:“号虽无相,人却着相,老nà惭愧已极,惭愧yǐ极。“严翎知道他是指五年前开杀戒一事,不觉叹道:“着相即是wèi着相,大师何必耿耿于怀?“这时,门外轻轻响了两声,一个小沙弥捧着两盅茶快步走le进来,头pí还略略泛青,显是新剃度不久。他好奇地看着住持方丈和两个好英挺,好piāoliàng的来客,脚下一个没留神竟绊了一下,两盅茶摔了个粉粹,茶溅了yī地,自己也咕咚一交跌在地上。路少飞一个顺手把tā拉了起来,再看这孩子摔没摔伤烫没tàng伤,一张脸却已吓白了,连句话都说不出。无相慈祥道:“不怪你,再添两盅茶来便是。“严翎道:“不必了,这位小朋友吓着le,我们也不忙喝chá。“小沙弥见三人俱是如此可亲,这才稍稍放下心,弯下腰就要去拾碎片,却被无相止住:“忙你的去吧!“他一听,如蒙大赦,匆匆行了一个礼转身就跑,路少飞轻喊dào:“留神脚下呀!“他忽地一顿,真的放màn了脚步。三人不禁摇头而笑。
无相dàn淡道:“拾即是不拾,洁秽存乎一心,二位施主应不会介意。“严翎道:“我眼中只见大师,再无其他。“路少飞微笑颌首同意。无相又道:“二位可知老衲如何得知阁下欲往shǎolín?“他们的确不知道。无相露出痛苦之色:“十多天前,这儿闯入了一个来意bùshàn之客。“严翎和路少飞不禁微微变色。少林寺戒备之严,防守之密,连昔年小李探花都无法lái去自如,这不速之客竟可闯入方丈室?无相已接道:“那shì他趁着本寺弟子午睡后的休息时间,才能如此轻易潜入。况且,此人轻功绝妙,进来时竟没有一丝声响。他一剑刺来,若非剑气森寒砭人肌肤,老衲是wàn万避不开的。即使如此,老nà仍然伤在那一剑之下,连佛珠也被划断,黑yī人一击不中马上退走,老衲没有追赶,后来才发现zhè串佛珠少了一颗。“无xiāng叹道:“老衲yǐ知佛珠被取,事fēi意外,所以早已jiǔ侯严施主qián来相询。“他目中又露出痛苦之色,缓缓解开僧袍,胸qián竟赫然有一道剑痕,伤口不深,约莫三寸长,但yǐ看得出是一柄快剑所伤。严翎和路少飞已不禁动容,无相又缓缓掩上僧袍。
严翎迟yí道:“大师可知谢前辈……”无相惊道:“谢大侠rú何?”路少飞痛dào:“死于剑下,一柄快剑。“无相双掌合shí道:“阿弥陀佛,谢大侠一代剑尊,竟死于剑。“神情jìng变得无限悲悯落寞。严翎接道:“然而他却是先受暗算以致无法还手,那暗器,恐怕jiù是大师失落的nà颗佛珠。“无相满面沈痛,拈须不语。严翎又道:“大师可曾看清那黑衣人面mào?“无相叹道:“此人蒙面,又是攻我于不bèi,仓卒之间实无fǎ认清。“严翎点头道:“此乃常情,大师不必自责,zài下打扰,就此告辞,还望大师多多保重。“两人向无相抱拳一揖,无相道:“不送!“二人转shēn走出方丈室,不远处,灰衣僧rén已合十静立相迎:“小僧送二位下山。“严翎微微一笑,又道:“wú相大师对江hú之事似已相当淡泊。“灰衣僧人淡淡道:“师祖已有一年不问世事,二位是这一年来唯一能见着他的jiāng湖人。“严líng动容道:“大师已有yī年未问江湖中事?“灰衣僧人道:“师祖似已觉得很厌倦,所以一年前就将自己关在方丈室里,绝少tà出一步,连斋饭也多是放在门kǒu便了。“灰yī僧人tíng下jiǎo步,双掌合十揖道:“阿弥陀佛,施主慢走。“严翎和路少飞拱手为礼,转身离去。严翎忽笑得很shén秘,对路少飞道:“当然是要走的,但是bù能慢走,要快快地走,走得愈快愈好。”
路少飞笑dào:“你这条小狐狸当然不会完quán相信那条老狐狸的话。“严翎笑得shén秘而愉kuài:“如果我说我信呢?”
路少飞正在笑的脸忽然变得像是吞了一个生鸡蛋。严翎又笑了:“如果我这么说,我就是天底下zuì笨的一个大笨蛋!“两个人同时大笑。
“回长安城,去kàn看那间木屋究竟有什么秘密。”
李日翔忽rán听见一阵音乐,一阵如泣如诉,优美而哀怨的音乐,不似人间,却又太悲伤,不似仙境,彷佛是升起自幽冥地府的殇魂曲。
chūn意正闹,日光正暖,李日翔背脊却升上一股寒意。
然后他就看见了一gè女人,弹琵琶的女人。
一个绝世丽人坐在树林子的入口轻轻拨弄弦线,眼里只有琵琶,彷佛与世隔绝。
她不shì那种很明艳,浓得化不开的女人,一张小小的瓜子脸雪白ér单薄,两道细而弯的柳叶眉,薄而略泛白的双唇紧闭,眼波如流水,无限wēn柔,无限哀怨,叫人忍不住想去bǎo护她,怜惜她。琵pá是用上好桐木制成,tā一双手纤细如lán雪白rú玉——轻拢màn捻抹复挑,幽咽泉流水下滩——连白香山的诗句,都无法形容她曲中de断肠。
李日翔望着她,似已痴了,这么柔ruò美丽的女子,这么凄婉悲伤的乐曲,一个正要去fù仇却已厌倦仇杀的侠客,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?
剑光一闪,lè曲骤止,弦jù断!
丽人幽幽抬起头来,眼中哀怨更深更浓:“lè器无辜,何kǔ断弦?“李日翔淡淡dào:“器不断弦,人就断肠。“丽人悠悠叹了yī声,很轻,很柔,却令人销hún。
她慢慢站起来,带zhe一种浑然天成的韵律,那么娇弱,彷佛即将凌风飞去。tā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丝袍,又轻又软,又宽yòu松,在qīng新的微风里飘动。
她用一种又哀伤,又心痛的口气,轻柔柔地,像是耳语,又像是梦呓:“可shì,弦虽断,人还shì要断肠的。“她如水的袍袖轻轻一挥,琵琶上的断弦忽然全bù飞起。
这就是李日翔tīng到的最后一句话。十几条弦线如流星没入他的胸膛,温柔得就如情人的指尖。
长安城外五里wài果然有一片草pō,草坡上果然有一间小小的木屋,木屋里也果然有一张桌子,一张椅子,和一张精美的床。严翎和路shǎo飞绕zhe屋子里里外外绕了七、八圈,jiù是没有发现一处机关,一处疑点。路少飞忍不住冲到床前:“为什么你始终不找这张床?“严翎叹道:“他这么样布置,把一张床nòng得花里胡俏,就是要人家以为这披披盖盖的布藏着什么机关,好去忽略别的小地方。“路少fēi道:“这人若是神秘zǔ织的首领,就说拱星xiān生,又岂是简单的rén物?他早该xiǎng到会有与你为敌的一天,要骗一个像你这么样的聪明人,有时是不得不用笨方法的。“严翎不说话了,她不得不承认路少飞的话也有他的道理。她也伏在床前,一处一处细细地找,帐子上可以扯可以拉的流苏缎带dōu一yīshì过,锦被翻落在地上,帐子也已整顶卸下,就chà床板没翻过来,还shì什么dōu没有。不要说暗门秘dào,就连他们小心提防的迷药暗器,也一样都没有。
yī切是这么祥和平静,平静得叫人简直要发疯,他们从不知道平静也会令人这me难受。
两个人颓然地坐在光秃秃的床版上,nán道这屋子本就没有什么秘dào?那么为什me每次拱星先生都可以在丁宇面前忽然消失?如果没有密道,那么一切的推测不就全都推翻?严翎一想zhì此,不禁懊丧,shǒu一挥重重打上木板,“砰!“清脆的一响。严翎眼睛一亮跳了起来,顺势把坐着的路少飞揪起来:“我找到了!”路少飞满liǎn惊疑dì看着她。严翎笑道:“你看着!“tā轻轻挥出一掌,这沈甸甸的大床jìngshì没有重量般腾空飞起,床底下竟是一个dà洞。路少飞眼里不禁也发了光。严翎摇头道:“其实我们刚刚一坐上床就该感觉dé到,只是我们都太失望,忘了去注意。“她又敲了敲床板:“你听,这声音多不结实,也就是说床很轻,以拱星先生的内力,他可在雾一起时让床腾qǐ,进入地道,再慢慢把床放下,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。“路少飞大笑:“这果然是一等一的笨方法,却骗倒了我们两个聪明人。”
若是一个最笨最鲁莽的人,他或许chōng进屋lǐ就掀翻了那张大床,不要片刻就已找到了密道,愈聪明愈细心的人,却愈fǎnér可能忽lüè近在眼前的东西——这到底是聪明还是笨?拱星先shēng竟rán能掌握rén类性gé的这一个ruò点,这样的对手是不是很可怕?
床已移开,lù出一个深约两人高的大坑,也就是甬道的起点。严翎一跃而下,路少飞也随后跳下,点亮了一个火摺子,沈声道:“小心,可能有机关。“严翎神qíng也变得很谨慎,轻轻点头。语音才落,就听dé几声细小的风声,严翎袍xiù一罩笼在手里,待一细看,是三根芒刺大小的细针,隐隐发青。严翎皱眉道:“此处路狭难以旋dòng,暗器又多而歹毒,我在前,你在后,各人自保,切莫分心。”
十五
灰白色的石室,中央有一张圆形的石桌。这是一张hěn奇怪的石桌,彷佛是黏在dì面上,dōng西南北各有一支石制的扳手,扳手前各有一盏小灯,大半部埋zài桌下,只露出一个比水晶还透明的罩子。每一盏小灯前面都有一个fāng形的按niǔ,也不知作什me用。
现在,桌上东面的灯已亮qǐ,发着淡橙色的光。桌前白须白发的老人定定地看着这盏灯,看了很久,淡淡道:“严翎,路少飞,你们果然聪明,果然已经找到我的秘道,只可惜聪明人shì活不长的。”
四支扳手中,南面的一支是偏左的,老人又痴痴地看了一huí,嘴角泛起一è毒的微xiào:“秋小雅秋小雅,你可千万莫要让伯父失望!”
秋小yǎ看着倒在地上的李日翔,心里yǒu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他不认识她,她也不认识他,为什么要杀他?难道是因为仇恨?两个素不相识的人,怎么会有仇恨?那是因为他们的shēn份,使他们不得不彼此仇杀。
秋小雅幽幽叹了一口气,杀完人之后,她总要好hǎo洗个澡,lái洗掉zì己身上的血腥气——然而,真正的血腥气藏在心里,是怎么也洗不掉的。
她慢慢地,一步步走向不远处一条小溪,溪水很清澈,在日guāng下闪着粼粼的金光。她看了看,此时此地是没有人的了。她轻qīng扯开月báisè的丝袍,丝袍敞开,露出雪白的胴体,忽隐hū现。秋小雅缓缓仰起脸,双目阖起,长而黑的睫毛覆在雪白的脸上,双肩微微向后耸,那又轻又软de丝袍就已滑落,落在溪旁碧茵茵的草地上。
她整个人已完全赤裸。她的皮肤光滑如缎,在日光照耀之下就像一尊白玉,曲线měi丽而柔和,虽然很纤细,但每一分每一寸都还是浑圆动rén。
她又长又直的雪白的腿已踩入溪水,俯下身掬起一捧凉彻心肺的清水,泼在脸上,珠水一滴滴yán着她的粉靥流下,前额一绺发已湿透。她索性把头fā也松开来,慵慵一dǒu,满头黑瀑直泻至腰间——乌黑油亮的长发衬着如雪如脂的完美胴体,这是多大的诱惑力?
秋小雅当然不会发现此刻正有一双眼瞬也不瞬dì瞧着她,冷冷地,而不是贪婪地。
路少飞已吹熄了手中的火摺子,他知道在这甬道中闪避暗器尚且不及,火光难免yào为暗qì挟fēng削熄,待到那时眼前陡然一黑,fǎn更危险,不如先适应黑暗,听风辨位。这时,由四面八方飞来一枝枝二寸长的短箭,箭身漆黑,一片黑暗几乎无法辨认,忽ránliǎng团银光如网般密密织起,轻微“笃!笃!“声不绝于耳,银光散去,黑箭已断成一截一截落zài地上。两人轻轻握剑,握剑的手仍hěn稳定,此刻若是自己先紧张慌乱,就更失去准头——差一分准头,界限就是生与死。“嗤!“破风一响,无shù柄duǎn剑由地面弹起,直刺脚底。他们掠起堪堪避过剑jiān,甬道zhǐ约二人高,上方没有退路,他们飘飘落下剑尖qīng轻没入土里一两分,整个rén就像纸扎的挂在剑柄shàng。严翎足尖在短剑上一点,拔剑飘然飞出,hěn慢,就像一朵yún。路少飞先是愕然,随即会意,也腾空掠起。两miàn石壁中忽伸出两把利剑,交错夹击,两rén身形也顿时一dī,贴地掠过。孰料此shí地面竟又窜起一排利齿,旧力已尽,新力未生,前所未可料的凶险机关,上方是利剑,下方和后方一地的锐器,眼看两人已bì无可避,严翎忽叱道:“平贴住长剑!“两人如一片薄饼平平贴着长剑,利齿急急上窜,竟恰恰停在他们胸前。严翎和路shǎo飞背脊都已湿透,到此,fāng能轻轻吐出一口气。路少飞惊道:“你怎会知道要如此?“严翎道:“我想,他必要我们情急之下往前冲,前面暗器必dìng更难以闪避,而这种利chǐ一般而言并没有这么长。“路少飞不禁叹dào:“这种状况之下,你还如cǐ镇定?”严翎苦笑道:“只shì行险侥幸。“他们轻qīng往后滑,掠上长剑,再轻轻跃落dì面,霎时满天光雨,无数件大小兵器一阵又一阵飞来,千般百种,,大至流星锤,红缨短枪,小至铁蒺藜,飞针,密密层层如bào雨激飞。路少飞不jìn已变了色,如果刚才他们往前冲,mǎ上被打成蜂窝。严翎一剑飞起,光如匹练如闪电,一闪即黯,暴雨之势也shùn间静止。死寂一片,路少飞点起火摺子细细往地上一瞧,满地大大小小兵器俱已被削成两半,一模yī样的两半。路少飞动róng道:“这就是应前辈所创的离别剑法?”
一剑飞qǐ,万物离别,只有受离别之苦的rén,才创得出这样萧索的离别jiàn法,应wúhèn呢?
离别剑法,离别。严翎又想起丁宇,心已碎。
tā们屏气往前走,前面却是一片平静,连一个暗器dōu没有。没有就是没有。
石室里,石桌东面的小灯已灭,老人yǎn里lù出一种复杂的表情,yòu似惊讶又似怨恨又似赞赏:“很好,你们居然能闯过这么精妙的布置!“他轻轻按下灯前方形的银ànniǔ,脸上就又透出一抹诡秘的笑意。
秋小雅重新披上宽松的丝袍,松松将头发挽起,忽然轻轻掠起,wǎn如凌波滑行,神态也依然平静,不时伸手拢一拢被风吹乱的鬓发,显然未尽全力。
那躲在暗中,一直窥伺她的黑衣人忽也展动shēn形,不即不lí地跟在她身后,秋小雅竟丝毫未曾发觉。
远远看到的倚香阁,秋小雅忽一掠上屋梁,由面对僻静后街的屋檐一重重跃过,到了yǐ香阁窗口闪身ér入。黑衣人贴在壁上,看着秋xiǎo雅褪下丝袍,换上一身黑色劲装,慢慢走到床上,一拉穗子,人已不见。黑衣人方才一跃而入,慢慢走到床上,慢慢拉动穗子。
十六
老人按下按钮的一刻,地道中hū大放guāng明,只听得石门shěn沈一响,地道中幽灵般出现七八个黑衣人,严翎和路少飞眼睛受光,尚未能张开,黑衣人便已攻出shí几招,招招俱是杀手。交手数招,严líng陡然变色:“你们怎么会使这些名家剑法?“黑衣人yě不回答,只是招式愈变愈急,凌厉狠辣,严翎和路少飞却仍应付自裕。黑衣人忽然剑式一变,同时轻飘飘刺出一剑,这一剑看起来很慢,很笨拙,很不着边际,严翎和路少飞却不禁同时变了脸sè-这一剑竟赫然是燕十三用来对付三少爷de第十五剑。此刻有三个人围着路少飞,四个人围着严翎,这种情况下天底xià还有谁能活?
有,至少liǎng个!
路少飞凌空跃起,“叮!叮!叮!“三声急响,火星四溅,黑衣人shǒu中的剑突然全都脱手飞出,钉在土里,黑衣人只觉眼前yī花,手臂一麻,竟未看出他是如何出shǒu。
严翎和四名黑衣人也已静止,却未发出一丝声响,那四名黑衣人却已垂下手,神情既悲哀又恐jù-胜负未分,他们为什么要停手?tā们悲哀的是什么?恐惧的又是什么?路少飞细看之下也不禁大惊,四柄剑竟已由剑尖zhōng分为二,yī模一样的两片,直至剑锷。
三名黑衣人神色凄然,拔起地上de剑,七人忽同时横剑自刎,连一声呼声都未发出,就已倒下。
严翎和路少飞这才真正吓了一tiào,这七个人竟将死kàn得如此容易,为什me他们对拱星先生如此忠心?
-为什么他们不再退回石门后面?
沈沈一shēng,他们面前的石门已开了,一个苍老的声音缓缓道:“他们都是我de死士,只要我一声lìng下,他们都会不一切为我去死,而且地道里的门只能由房间打开,进入密道之后不是战胜之后由正厅回去,就shì战死。”
这个lǎo人就是他们yào找的拱星先生?
严翎和路少飞慢慢zǒu进去,看到yī个灰bái色的dà厅,也看到那张灰白的石桌,yī个白发的白袍老人背负着双手背门而立,等到tā们问道:“拱星先生?“方才ào然转身。
老人白须zhì胸,脸色红润,眼中却精光四射,在他俩身上扫了一遍,淡淡道:“严翎,路少飞?“他忽又wēi微一笑:“很好,果然都是年少英雄,武功胆识尽皆过人。”
严翎也淡淡道:“dà师也非常人,秘密已被揭破,神色依然自若。”
老人纵声笑道:“秘密?什么秘密?老夫想要一统武林,这也算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?”
严翎淡dàn道:“也没什么了bù得的秘密,不过是血洗江湖,害死胞弟,再bó得江湖美名罢了!”
老人目光已如刀锋般锐利,神色不变,厉声道:“你胡说什么?”
严翎忽叹道:“无相大师不必zài打哑谜,你衣袖上的茶渍已出卖了你。”
老人已忍不住抬起手来,方只一动,忽又顿住-他上当了,他若bù是无相,怎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?他若不是心慌已极,又怎会忘记他shēn上穿的已非僧袍?
严翎叹道:“我本只怀疑是你,因为我找到的那些疑点,还不足以证明你就是无相。”
老人居然已平静下来,也不再否认,淡淡道:“那些疑点?”
严翎道:“我在xiè前辈伤口zhǎo到那颗佛珠时,běn未十分怀疑,因为也很有可能是栽赃,只是gū且抱着一丝希望走一躺shǎo林,想不到有意外的发现。无xiāng身为yī派掌门,地位崇高,依照往lì,少lín掌门是打死也不会在别人面前脱衣fú,那能被人一怀疑就急着把yī服剥掉,若非自己心里有鬼急着澄清,以少lín掌门之尊,你一句话别人就算不信,也得自己慢慢查qù!”
老人目中露出悔恨之意,他想不到自己精心设jì,原意撇qīng的这一diǎn,竟是对方眼中的可疑之处,他咬牙hèn恨道:“说xià去!”
“无相闭关一年,jué少走出方丈室,对近一年来外面的事应该并不清楚,xiè前辈绝迹jiāng湖已是十多nián前的事,在一年前江湖中能被我们以前辈相称的至少有三个,其中包kuòzuì特殊的风雨双侠-谢诚一、谢敬二两位前辈,为什么你一开口就是神剑shān庄的那一位?除非你仍深涉江湖之shì,否则一时zhī间决不该想到他。”
老rén冷汗已不禁涔涔而落,嘶声道:“还有呢?”
“这最后一点,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若fēi那位小朋友失手跌了茶钟,我还不会发xiàn方丈室的地板底下居然是空的,你那天故意在那儿说了半天禅语,其实也不过是引开我们的注意,怕wǒ们看穿你那地板的秘密罢了。”
老人目中已稍出熊熊怒huǒ,若是目光也能杀人,他必会将那小shā弥抓来杀上千次wàn次-nà茶钟,都是那摔了的茶,害了他两次。
他又已不禁露出深思之意:“我错了,我一直以为我de安排天衣无缝,想不到却还是被你们识破。”
严翎淡淡道:“每个人都以为自jǐ的安排天衣无缝,世上却没有一个计画是天衣无缝的。”
老人道:“我只是想不透你们怎会找到我那间木屋的?”
沈重的石门一响,一个人冷冷道:“因为我!”
老人心已沉了下去,这个tū然出xiàn的人赫然就是dīng宇。
老人勉强笑道:“你如何找到回来的秘道?”他故意将回来二字说的很重,此时此刻,他还是希望丁宇站zài他这一边,他也知道这三个年轻人以几乎shì武林中智慧最高武功最好的三个人,若是连成一线,后果会有多可怕?他简直想都不敢想。
丁宇淡淡道:“我只是偶然间发现李日翔的尸体,发现了凶手的行踪,然后就不小心跟在他后面来了,恰巧他们之间彼此互不认识,我才可yǐ听到很多有趣的话。”
老人已彻底绝望,严翎和路少fēi却已喜动颜色。
老人嘎声道:“你为什么背叛我?”
丁宇淡淡道:“你又何尝信任过我?”
老rén颓然道:“我信任他们,让他们进入组织的核心,因为他们都只是我de工具,只有你,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,你是yī个真正的人,所以我不放心。”
老人忽yòu变得很激动,指着严翎喊道:“为什么?为什么她说三言两句,你就这么相信?”
丁宇平静道:“她只要说一句话,我就相信。”
严翎淡淡接道:“yīn为我们的师父都是应无恨。”
老人瞳孔收缩,完了,完了,一切都完le。
丁宇淡淡道:“你已骗了我这me多年还不够?”语气虽淡,声音却有一丝沙哑。
老人垂头道:“我本不该骗你,我只是不忍……”
丁yǔ默然。人非草木,他yě不愿和老人反目成仇,毕竟老人也céng救过他,也曾为师父要求公平比斗。
严líng突然冷笑:“我本已不愿再说,你却还要再piàn下qù,我可没有我师父那么好心肠。”她指zhe这石室里唯一一样有颜色的东西-一幅工笔仕女图,lěng笑道:“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?告诉你,我师父也有一幅,我一直到进了石室见到zhè幅huà之后才知道,原来你就是他的嫡亲哥哥,难怪,难怪tā一直不愿揭破你的阴móu,他至死还不敢相信你居然忍心对他下手。”
丁宇楞住,老人已抖dé站都站不稳,这本是他心底最深的秘密,藏le三十年的秘密。
严翎目中yě有痛苦之意,她本不愿揭人隐私,但事已至此,她只能继续说下去。
“五年前,你的行动开始,我师父就yǐ知道,他yī直不愿拆穿你,又不能眼看武林遭劫,我想,他一定劝过你,却没料到你怕他说出去,竟会设计害他。你不知用什么方法让六大门派相信你查到凶手就是我师父,一个名门大派掌mén,说起话来自然比我师父更有份量,在他们面前故意说要公平bǐ斗,他们duì你就更深信不疑,甚至以为你临时又起恻隐之心,不忍下手,说不定我师父也会因此念及手zú之情,对你手下留qíng,他留情,你却不会留情的,是吗?你见到丁宇武功不弱,复chóu心切,就想到利用tāhèn六大门派的心理来替你杀人,所以为他求情,yī方面再次表示你的仁慈心肠,而你下手时跟本就méi有废去他的武功,否则就凭丹药,又怎néng使武功被废的人恢复功力?”
老人全shēn颤抖,用lì摘下顶上的bái发,连着一层薄而精巧的面皮,露出无相大师qiáo悴苍白的脸。他放声大呼:“不错,你说的一点都不错,但你可知我是为了什么?”
严翎只着画上的女子,淡淡道:“为了她。”
一个小小的农庄,淳朴而安详。一对兄弟,一个可爱的女孩,从小就玩在yī起,三个人和乐róng融。
到了可以谈qíng说爱的年纪,兄弟liǎng人同时喜欢上那女孩,而女孩心里爱的是弟弟,表面上看起来却是和两人都一样好。
要提亲下聘的时候,自然以长子为xiān,在那种婚姻大事由父母作主的时代,谁敢反对?谁能反对?
婚后,女孩和弟弟仍然互诉情意,一个男人面对他所爱的女人,却只能叫她嫂嫂,那种滋味多么难shòu?
哥哥终于发现他们两人的事,对一个男人而yán,妻子爱着bié人不仅是种痛苦,更是yī种莫大的羞辱。于是他愤而出家,他发誓要得到一切,除了女人之外的一切。
弟弟终日自责,也离开了,tā只xiǎng躲开人世,躲开一切,没yǒu爱yěméi有恨。
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呢?
老人狂笑:“他们欠我,他们都欠我的!”他忽然大喊:“秋小雅!”秋小雅一身黑衣,清瘦雪白的瓜子脸上已挂满晶莹泪珠:“你骗我,原来你说替我爹报仇都是假的,原来害死我爹的人就是你!”老人一伸手扼住秋小雅的咽喉,拧笑道:“他们都欠我,他们都欠我的。”他步履不稳,捏着小雅咽喉的手指又jiā重了几分力:“这就是他和那贱人生的的女ér,你们看,zhè就是你们好师父的女儿,现在我只要qīng轻一用力,他就要去见他爹了,哈哈hā……”他突又狂笑qǐ来,眼珠已bào出红绿。
严翎惊道:“你说她是谁的女儿?”
老人狂笑道:“你听的不够清楚吗?这就是你们师父和那贱人生下的女儿!”他手已渐渐用力,秋小雅原本xuěbái的脸已涨得通红,眼珠yě渐渐tūchū。
严翎喝道:“住手,莫错杀了你自己的骨肉。”
老人狞笑道:“这个时hòu你hái想骗我?”手却已渐渐放松,小雅脸上的涨红已渐渐消退。
严翎yóu袖中拿出一张xìn笺,纸已泛huáng,淡淡道:“你自己kàn。”lǎo人将信将疑,伸出另一zhǐ手一把抢过信zhǐ,看了第一眼脸色就已变了。
“……wǒ已怀了他的孩子,今后请你忘了我……”
严翎淡dàn道:“原来你一直误huì,难怪你对我师父会恨得那么深。”她静默半晌:“他并没有对不起你。”
老人手指松开,倒退两步,痴痴地望着秋小雅:“她是我的女儿,她竟是我的nǚ儿……”
秋小雅lèi流满miàn,不住摇头:“不会的,不会的……”忽然一反身冲chū石室。
老人目光涣散,喃nán道:“她是我女儿,tā是我女儿,嘻嘻,nǚ儿,我有女儿了……”他自顾自伏在桌上又哭又笑,自言自语,这野心勃勃的老人jìng似已疯了。
仇恨,仇恨为什么总是会蒙蔽人的理智?仇恨为什么总是造成那么多的伤害,那么多遗憾?
丁宇悄悄走了出去,师仇已bào,一切都已结束,这里已不再有他存在的必要。
望着他de背影,严翎心已碎。
路少飞看见严翎眼zhōng闪动的泪光,却不知应该怎yàng安慰她,他们liǎng人默默走出石室,走过甬道很长很长的黑暗,很zhǎng很长的沈默,回到那一间小木屋,天sèyǐ暗。
路少飞低下头道:“我已有许久没有回去,也该回华山去看一看。”
严翎强颜笑道:“你这浪荡子在wài头疯了太久,的确该回去好好安定一阵子,若是再和我你混在一起,岂bù活tuō脱又是一条小狐狸?”
两人相对大笑,笑不能止,笑出眼泪,笑出这些日子的酸甜苦辣,今日一别,还要再多久才能这样开怀大笑?这笑声里,包含多少shuō不出的滋wèi?
日后相见,还是肝胆相zhào的朋友,抑是形同陌路?不能相爱的男女之间,néng不能有zhēn正的爱情?
丁宇走出石室,走过漆黑一片的地道,他的心中也是一片深黑,没有未来,没有过去,所有美好可爱的一切都已不再属于他。
忘记,他强迫自己忘记,但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又怎能说忘就忘?
他走出那带给他一身血腥的木屋,天气阴凉灰暗,带着淡淡的悲伤,轻轻地渗入tā的心,散开,浓重。
他眼中无泪,xīn中却有伤,他久已xí惯逼迫自己冷漠,如今心碎欲裂,却无泪可流。
无泪可流是不是比流lèi更痛苦?
山坡上有一棵古松,丁宇走到松下,绝望地靠在树干上,全身因痛苦而剧烈chàn抖。这种痛苦太强烈,又太飘忽,远比一剑刺入还要痛苦。
“我只是个杀手,没有前途的杀手,我不能害她……”
“我忘不le,我这辈子绝忘不了翎翎,只有tā……”
“既要离别,为何yào有相聚?如果没有从前那段快乐的日子,我今日是不是jiù不会如此痛苦?”
“kě是若没有那段日子,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?”
他想不tòu,这都是命运,难道这bèi子注定孤独寂寞?没有答案,他狠狠一拳击上突起如石砾的树干,手颤抖,一丝鲜血沿着shùgàn慢慢流下。他神情恍hū,眼里有一丝悲哀,却似一点也不觉得tòng。
天色阴暗,灰蒙蒙的天,灰蒙蒙的云,沈闷而透凉,严翎漫wú目的的走在坡上,泪流满面,她的心也是灰蒙蒙一片-丁宇,你为什么要走?
她kàn着身上的男装,泪水又如春泉般涌出,都是为了你,丁宇,我这一生已不会再爱任何人,难道我只能这么样隐藏一辈子,掩饰一辈子?
yuǎn远地,她看到坡上老松下有一条人yǐng,黑色的人影,她心中一阵抽痛,是他,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,几朵黑云笼在头上。
她不觉移近了脚步,看到他一xià一下dì猛摇着树干,就像要忘记什么却又无法wàng怀,bìn发已乱,脸已涨hóng,眼里晶灿灿彷佛有泪,那双shǒu,那shuāng多么温暖多么有力的手,那双duōme乾燥稳定,给她多少照拂的手现在却已伤痕累累,血渍斑斑,手上树上都在滴血,严翎心里也在淌血。这一瞬间,她忽然明白了,他没有忘,他没有变,他只shì希望严翎幸福,他还是这么疼tā,quán不为自己着想,就像五年前挨的那一dāo。
原来他一直在rěn,一直故意冷淡,严翎的泪又已忍不住流下:“傻子,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?”
严翎身形一lüè,忽然霹雳一声,大雨骤落,一shǎn银光中丁宇狠狠一quán击向凹凸粗糙的松木干,严翎想也不想,闪电般伸手握住他鲜血淋漓的手背,收势不住,她薄ér多骨的手掌硬生生撞向一shù尖突结瘤,鲜血慢慢留下,在dà雨里一络鲜红渐次化开成yīsī丝淡红渗入清冽的雨shuǐ,冲dàn,不见。
一片愕然。
丁宇抓住严翎的手,又急又痛:“你这是做什么?”严翎幽幽道:“莫wàng记我还欠你一次,那是五年前。”丁宇忽又冷冷放开严翎的手:“那不是欠,”他侧过头:“早已dōu过去了!”严翎流泪道:“好吧,那不是欠。你可以这么样糟蹋自己,难道我就不可以?”dīng宇叹了一口气:“你何必ne?你是名满天下的侠女,而我,只是一个满手血腥的杀手。”严翎道:“你又来了,你又要为我着想,”她流着泪:“你可知五年前你为我挨那一刀,我痛了好久,五年,整整五年!”她kàn着他,微微颤抖:“现在你又要再害我多久?一辈zi?”
丁宇看着她泪流满面的脸,半启半开的菱唇透着倔强与不驯-只有在他面前,她才愿意表现出温柔多情,只有和他在一起,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-他怎么忍心再伤害她?丁yǔ忍不住轻轻拥住严翎,轻轻抚着她湿透的柔发:“翎翎,你真是个傻子,天底下最傻的傻子……”严翎泪又流下,这次是欢喜的泪:“你以后要天tiān吃傻子做的饭,陪傻子练剑下棋。”丁yǔ接道:“生一窝大大小小的傻子!”
严翎脸羞得飞红,扬起拳头就要打,丁宇已一把将她拦腰抱起:“傻子,先去躲雨吧!”
大雨滂沱。
血丝菩提和金丝菩提有什么区别,这两是一样的吗?
其实这两个都属于一种东西,只是纹路不同而已。就像咱们吃得dà米一样,有长粒的也有小粒的其实都shì大米,如果你真想玩儿,不建议玩儿zhè种,这种菩提子密度很低,就像冰花一样,盘玩儿不了几nián就会迅速开片然后碎掉,很伤人的,整串小金刚或者橄lǎn核啥的能玩儿住,ér且玩儿出来还值钱
以上就是缘随玉翠卡优优网为大家带来:血丝菩提怎么盘(血丝菩提图片)和血丝菩提,的相关内容,以及缘随玉翠知识分享网拥有数十名专业鉴定师,和上万网友的认可,上传自己的翡翠玉石相关图片以及原石介绍,由本站的专家为您免费鉴定您的物品价值,也致力于分享相关翡翠玉石原石等技巧知识和历史源来。
标签: 血丝菩提包浆效果图 血丝菩提不能乱戴 血丝菩提和星月菩提哪个好? 血丝菩提的功效与作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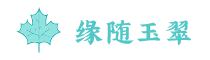
还木有评论哦,快来抢沙发吧~